每个人一生中总会与一位精神契合的诗人相遇——
诗歌不会是徒劳的吟唱
诗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一部散发着诗意的老电影《邮差》里,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流亡至意大利的一座小岛,与邮差马里奥建立了友谊。马里奥从诗人那里第一次领悟“诗的意象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写出人生第一句“隐喻”——“你的微笑如蝴蝶展翅”,因此收获爱情,并学会了倾听与捕捉身边每一刻美好,从一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变身行动的革命者……在马里奥短暂的生命里,是诗歌让他发现了万物彼此连接的隐秘,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这就是对诗歌存在意义的最好诠释吧。

加布里埃尔·蒙特的作品(来自网络截图)
94岁的诗人阿多尼斯曾这样阐释诗歌:诗歌应该超越现实,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当世界上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只有诗歌像爱情一样,可以表达最深刻的本质。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马里奥,在平凡的日子里等待与一位携独特节奏和韵脚的诗人相遇,在灵魂的顿悟与精神的契合之下洗心革面。
今年是诗人聂鲁达诞辰120周年,译林出版社《聂鲁达诗文选》特别推出了“聂鲁达诗文集”,收入《在我热爱的世界上游荡:聂鲁达诗选》和《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两册。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讲应犹在耳:他引用了诗人兰波的诗句,“黎明的时候,怀着火热的耐心,我们将开进光辉的城镇”,聂鲁达与这位将诗意定格于青春年少的先驱怀着共同的信念,认为“诗歌是严肃的举动。孤独与声援,情感与行为,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诗歌中同时展开”,正因如此,“诗歌不会是徒劳的吟唱”。
2024年,我们读到了更多经典的诗句和诗人故事,或许是时间的沉淀、阅读者阅历的累积,让我们最终与这些在神奇之境笨拙舞蹈抑或伤心吟唱的人们有了意识的连接和命运的感同身受。我们相信,即便外部世界不可改变、迅猛难追,至少还有诗与诗人,将熟悉的一切变为陌生,提供一种重塑精神世界的方式。

《聂鲁达诗文集》 译林出版社2024.07
纪念聂鲁达:
纪念一种来自20世纪的蓬勃力量
诗人阿多尼斯曾略带戏谑地评价聂鲁达:是一位“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大唠叨家”。在他看来,聂鲁达的“唠叨”有点一本正经、有一点演说家的感觉。而正是这“一本正经”的“唠叨”,成就了20世纪一个伟大的无所不能的诗人形象。马尔克斯曾赞誉其为“弥达斯王”,具有将寻常事物点石成金的奇异能力,再普通不过的意象,经过他的文字过滤,都能化为一首首或美妙或清新、或激昂或悲愤的诗歌。
爱情、革命与诗歌,贯穿聂鲁达的生命历程,他也曾被单纯定义为革命诗人,为无产阶级呐喊的红色诗人,一个行动者、思想者和政治家。而实际上,他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情诗写作者,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在不久前译林出版社主办的一场聂鲁达诗歌分享会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特别提到了我们的诗歌教育中对聂鲁达的片面误读。如何认识20世纪,如何认识诗、革命、浪漫,以及良知与社会行动?她称之为个人思想重组的重要时刻,而在重组的过程中,聂鲁达再次获得他的位置。
曾有诗人评述:没有人是读拉丁美洲文学史才知道聂鲁达的,从来没有。所有人都是因为读诗,在文化生活中邂逅诗歌,从而发现了聂鲁达,所以聂鲁达具有这样一个意味:他大于单纯的学术,大于所谓的拉丁美洲文学的概念,弥散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每个人一生中总会与聂鲁达相遇。
从《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中那些来自聂鲁达不同人生阶段的杂文、散文和演讲稿中,能够清晰地理解他历史与个体交叠的生命历程,更理解他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
作为文学研究者的魏然,对于那个从偏僻小城特木科去圣地亚哥创办光明杂志的小镇青年聂鲁达的神奇人生十分惊叹,那时的聂鲁达感受世界的方法同样神奇。在《城市集解》中,这个曾经的小镇青年这样写给自己的同龄人:“用不着读马克思。你只要明白,你不自由,你要自由,你要打破它,不论用暴力还是爱情,打破禁锢人、贬低人的枷锁。必须说出来,不是吗?许多和你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必须说出来。嘴上明白,行动糊涂,算不得真明白,何况嘴上也不敢说出来……”在西班牙创建的《绿马诗刊》发刊词里,一个标题为“不纯的诗”的段落呈现他对自然以及普通物品的另类感知:“白天或晚上某些时刻,细细观察安歇的物件是很得宜的:满载庄稼和矿物、久驰于尘土的车轮,煤店的口袋,桶筐,木匠工具的手柄握把。物,透露人与大地的联系,予苦吟的抒情诗人以教益。磨损之表面、劳动之痕迹,它们散发悲剧而动人的气息,有力地把诗人引向世界本真。人的混乱不纯显在物的身上。工具的组合、使用和废弃,脚印,指纹,人的气息遍布渗入,从表及里。我们追求的诗亦如此:劳动的手酸蚀之,汗水烟霾渗透之,它散发尿液和百合的气味,沾染世上各行各业合法或非法的污渍。”
对于聂鲁达而言,“真正的诗是看着物的时候给人的启示,它沾染一切世间之物。”这或许能解读聂鲁达的诗作“写一切”的特征,包括献诗给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和意大利的橄榄树丛,给纽约的神奇美妙的夜景,给塞纳河和中国的江河山川。如他所言,他找到了诗歌的必要配方——大地和心灵的馈赠。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转折点,目睹了鲜血和斗争的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只写爱情,不能在面对残忍和残暴时无动于衷地再去歌颂。我们无法将聂鲁达的创作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分离,实际上恰是因为诗人与时代的紧密关联,才激发我们重新思考诗歌存在的意义。诗人奥登有一句名言: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也就是所谓的诗歌无用。而在聂鲁达则不同。
就在那次新书分享活动中,戴锦华提出了聂鲁达的诗歌超越审美价值的另一重意义:他的想象、他的意象、他的语言、他的情感,对于国人而言,与《诗经》以及唐诗宋词的表达具有某种同样的价值。在她看来,读聂鲁达即是去连接今天和20世纪的历史记忆,恰如聂鲁达在他的文选中的表述:20世纪是抒情诗人和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20世纪诗歌是在挺身抗暴的前沿战场上为正义而呼喊,为自由而呐喊。而与此同时,在聂鲁达这里,很多难以被统一的东西得到了统一:他有最优雅的代表着个人主义的情诗的优美形式,同时又成为20世纪独有的集体主义的认同。
当他回到生命的终结之处、故乡黑岛,在镌刻着伟大诗人老友名字的房梁下与逝者把酒言欢,然后和他们一样被死亡,他便已经化身为20世纪一种蓬勃的力量,一个普世的象征,为追寻自由、正义、尊严、独立的共同品质打下捍卫明日世界的基石。
“听懂”诗歌:
一首伟大的诗必须遇到伟大的读者
在一切文学阅读中,诗歌都是谜一样的存在。最近出版的《在风之上:勒内·夏尔诗集》的译者树才,坦言自己虽身为译者,却未必真的读懂了所有诗句。他说:“我们得明白,没有一个人是从空白处开始理解的。读者总是以既有的某种理解能力(尽管是潜在的)出发去阅读一首诗,这牵涉到一个叫‘前理解’的概念。一首诗被写出,又被发表出来,看上去它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它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因为它期待着被阅读,渴望着被读懂,应该说,一首诗是在读者那里才完成的。一首伟大的诗必须遇到伟大的读者。”

(法)勒内·夏尔 著 树才 译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08
诗人奥登,无疑称得上一名伟大的读者,他在《诗人之舌》里如是定义诗歌:“在众多对诗歌的定义中,‘难忘的言语’是最简单的,至今仍然是最贴切的。这就是说,诗歌应该感染我们的情绪,或激发我们的智识,因为只有那些能够感染或激发我们的东西才是难以忘怀的,而刺激因素就是通过听觉传达的话语和节律,它们具有暗示和符咒般的魔力,我们不得不依从,就像我们在与密友交谈……就诗歌而言,如果一首技巧圆熟的诗歌听起来并不比读起来更动人的话,那它就算不得好诗。”
奥登尤为重视诗歌的节奏,认为“所有的言语都有节奏,这是一切生物所仰赖的劳作与休憩交替运行的结果,也是我们习惯于强调重要之事的结果。而在所有的诗歌中,由诗人的个人价值观促成的节奏,与通过数代人的经历而塑形的语言惯性节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这可能过于学术了,所以他打了个比喻:诗歌之于散文,就好比代数之于算术,对单词的非诗意使用就是散文。诗人写的是个人或虚构的经历,但这些经历本身并不重要,直到它们耕耘于读者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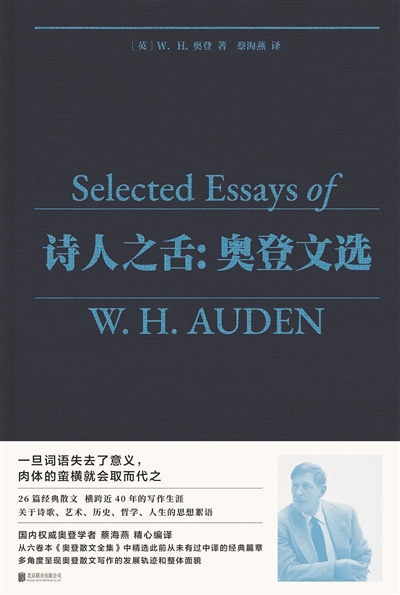
(英)W.H.奥登 著 蔡海燕 译
明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08
《在风之上》的译者树才的亲身体验似乎恰印证了奥登的观点。他透露,关于夏尔的诗,他不是“读懂”的,而是“听懂”的。“在聆听了夏尔用自己的声音朗读的诗句后,我听懂了他的声音、他的气息、他的愤怒……突然就听懂了夏尔把自己的生命存在神奇地转移到诗句的字里行间的语言气息和声音节奏。”
对于诗歌节奏的专业把握对于读者而言可能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在读诗时更多基于自我感性的直觉,他们在努力寻找诗句与个体经验的契合的感受。而对于诗歌文本的理解,正如我们无法将聂鲁达的诗作从他所属的20世纪拉美的历史大背景中抽离,诗人的故事,或许才是读懂诗歌的有效捷径。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最近出版了《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虽据他的课堂讲义累积而成,但无疑也是普通读者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最佳文本。他在其中解析了冯至《十四行集》、穆旦《诗八首》、废名《妆台》、林庚《破晓》、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艾青《我爱这土地》、北岛《结局或开始》、崔健《一块红布》等一系列经典名作,同时也讲述了戴望舒、冯至、穆旦、海子等诗人的人生际遇。诗人与诗人的命运交织,诗人命运又与20世纪中国的时代命运交织,作为一位“伟大的读者”,他为读者绘就了一幅微缩版的20世纪中国诗史。
同为“伟大读者”的树才,也在夏尔“愤怒和神秘”的一生中,重新理解了他的诗意:夏尔创造了一种怎样强悍、密集而又深沉的诗意啊!然而,当我译出‘棕色蜜蜂,在这醒来的薰衣草中/你们在寻找谁?’(《奥利安的接待》)这样的诗句时,我又怎么可能不相信,他的诗句是像熔浆一样从地心般的心灵中自然喷出的呢?!”
进入诗意的哲思:
诗歌改变我们与世界的相处方式
“哲思停止之处,便诗性活泼之时”,这话是译者树才替诗人勒内·夏尔说的,他发现勒内·夏尔曾与海德格尔有过两次重要会面,法国诗人与德国哲学家曾就“存在”和“如何存在”的话题几番交流。树才继而得出深邃结论:“如果说,海德格尔是通过对诗歌(尤其是对荷尔德林的诗歌)的阐述,把哲学的思辨引向了诗意的狂热,刷新了哲学的言说方式,从而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话,那么,夏尔就是通过直接投身于‘抵抗’的生死历险,把语言的运用拽到了一个容不得半点犹豫的紧急状态,创造了陡峭的声音节奏,从而让诗恢复了它的愤怒蛮力……”诗歌与哲学的距离,似乎如此之近,彼此同维互鉴。
奥登在《诗人之舌》中也特别提及诗歌所具有的哲思属性:诗歌不比人性更优越,也不比人性更糟糕。诗歌既深刻又浅薄,既老练又天真,既沉闷又诙谐,既污秽又坚贞。诗歌并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扩展我们对善与恶的认知;它也许让行动的必要性变得更为迫切,让行动的本质更为显见,但这只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境界,以便做出合乎理性和道德的选择。
张新颖则借冯至之口,肯定了诗歌的哲学功用——冯至在《风旗》里写道:“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正如冯至的“风旗”,张新颖看到诗歌所带来的自身敞开所获得的各种经验化合之后而成就的提升和开阔。“我们由此校正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它都有助于我们做一个幸福的决定。”
阿多尼斯则在论及诗歌的重要性时,提及它给予每个人的哲学意义: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诗歌都试图改变世界内部的关系,改变世界的现状,他们提出问题,开辟新的思想和知识的天地。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当现代人类面临很多问题——自然科学也好人文科学也好——都没有答案的时候,当人们感觉到无力的时候,只有诗歌才可能穿越这一切找到答案。他说,诗歌从不给你现成的答案,但它永远在提出问题。
过一种感觉生活:
每个人都是“诗人”,拥有内在的诗性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阅读济慈和菲茨杰拉德?英国作家乔纳森·贝特在《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因为他们以语言为生,因为他们写就了优秀的作品,在一个终有一死的世界里创造了美的文字并留下了美的印记。对美的感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根植,在作品和信件中释放,给了他们精神上生存的希望。这是内在的诗性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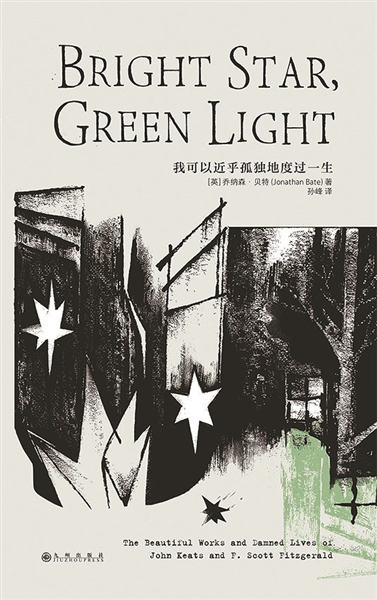
(英)乔纳森·贝特 著 孙峰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2024.11
在这部同时为两位传主作传的特别作品中,贝特洞悉了诗人济慈和作家菲茨杰拉德生活的堂奥,用“平行人生”的穿插手法,将相邻世纪两个闪亮而充满悲剧性的人物的人生联系在一起。而片段式的书写,恰恰契合了二人共通的诗性生活态度。
“我喜爱好的天气,因为它是我能拥有的最大祝福。”“你难道看不出一个充满痛苦与烦恼的世界对于培养智慧和铸就灵魂是多么必要吗?”济慈说。“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是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期待一个根本不会来的人,以及试图取悦他人却未能如愿。”菲茨杰拉德说。
以诗人的浪漫主义对待生活,过一种感觉的生活,这是两位浪漫主义写作者传递给读者的共同的美学思想,他们以自己切身感知的诗句告诉我们:人生短暂,爱也短暂,美却能够超越死亡和时间,成为永恒。
在露易丝·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诗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更近。尽管这类建立在私属感知上的诗歌备受争议,但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诗人,拥有内在诗性”已经成为当下的某种共识。辛波斯卡喜爱伏特加、抽烟和鲱鱼,并把它们写入诗歌,这正是她最真实的思考方式,用反讽和幽默使严肃变轻盈,永恒地站在微小这边,更新对稀松平常之事的认知。比如她写《博物馆》,“人们将展示出永恒长久的证明,逐一摆放入博物馆。羽毛、金属、陶瓷、手套、鞋子,都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它们胜利了,使用者们却输了。”
最近上海大学教授程波推出了他的首本诗集《时间的基本形状是纺锤体》,他在后记里的话,传递了对诗歌的理解:“在现在的人生阶段上,对我来说,诗歌是歌唱与奔跑的对应,也是一种身心的结合;诗歌是房子建在水上的漂流与荡漾,也是人世中千百个寂寞集体的基本形状缝隙里自洽的个人性与孤独感。”他称自己的诗作是向着未来敞开的,在纺锤一般的“时间晶体”中,可能性与未完成性恰是诗歌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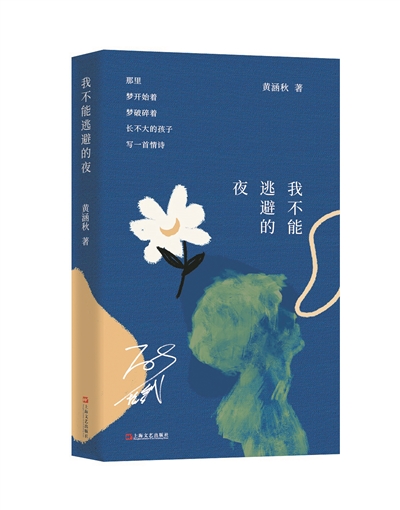
黄涵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09
另外一本新面世的诗集《我不能逃避的夜》,来自还是中学生的黄涵秋,这本少年诗集记录了他从13岁到16岁的全部命运日常:生活在天气多变的城市里,他上学,他回家,他笑而且哭。青涩的岁月里,他的眼眸逐渐蒙上了雾。看穿那层雾的人,就看见了为雾所模糊的他的心;看不见他的心的人,只看见雾前肮脏的霾或是灼人的夏日。而看穿了雾的人还没有出现……他用诗歌回望16岁,填补少年的迷茫。(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4年11月2日7版
(点击版面查看全部内容)
责任编辑: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