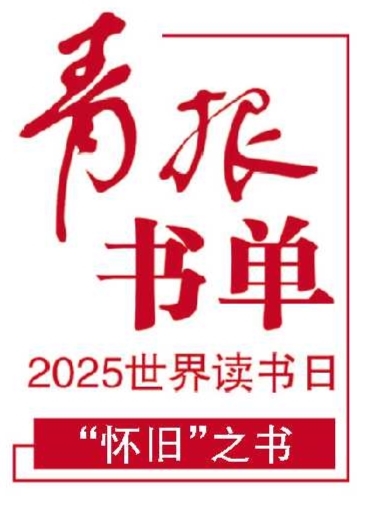
任何一个梦、任何一种念想都不会被真正忘记,所以我们“怀旧”——
记忆是一座博物馆,我们都陈列其中
弗洛伊德说,任何一个梦、任何一种念想都不会被真正忘记。如若此言不虚,那么人类的记忆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规模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将我们所经历、感知与思考的一切人、事、物秘密归档,又在某个特定时间将它们调取出来,重新赋予意义。如此往复,承载着无数被叠加与全新命名的共同记忆的我们,才成为我们。
《逝物录》的作者、德国“80后”作家、艺术家尤迪特·沙朗斯基相信弗洛伊德的话,在她看来,只要开始在记忆系统里寻找这些归档的人、事、物的痕迹,真相就不可否认,“连同被驱散或清除、被改换成错误甚或托付给遗忘的那些,也永远在场”。于是她将记忆写成书,犹如创造一颗开放的时间胶囊,将流逝的时间之痕记录下来,“让过往的再现、遗忘的还魂、喑哑的说话、被错过的得到悼念”。
如沙朗斯基所言,“书写什么也不能挽回,却让一切都可能被体验,它让人隐约感到,只要有记忆,在和不在的差别或许就不那么重要,存在和逝去的边界,正在于记忆。”所以,我们在书写中“怀旧”。
一张“怀旧”书单,关乎消逝。在一个记忆过载、渴望占有的时代,我们用消逝之物,探讨逝去对于生命的意义,以个体生命的回望,遴选与重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久违的深情传承一份承载美好与澄明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毕竟,在记忆这座博物馆里,我们每个人都陈列其中,都有不可复刻的有温度的珍藏。
“失败”的消亡之物
“怀旧”,意味着过去的丧失与消亡。而对于消亡之物的描写,《逝物录》无疑是一部展现想象力的经典之作。德国“80后”作家、艺术家尤迪特·沙朗斯基以消亡之物自身或其见证者的第一人称,讲述彼时彼地消失的“真相”。让读者沉浸体验“里海虎”于古罗马角斗场上残酷的生死一战;物理学家于中世纪小城村落追踪独角兽的无果;17世纪建筑大师如何建成了他的代表作、早已不复存在的萨切蒂别墅;公元前600年女诗人萨福留存于莎草纸卷上已不为人知的诗意;消失于历史深处的19世纪植物学家兼天文学家C.A.基瑙和他眼中的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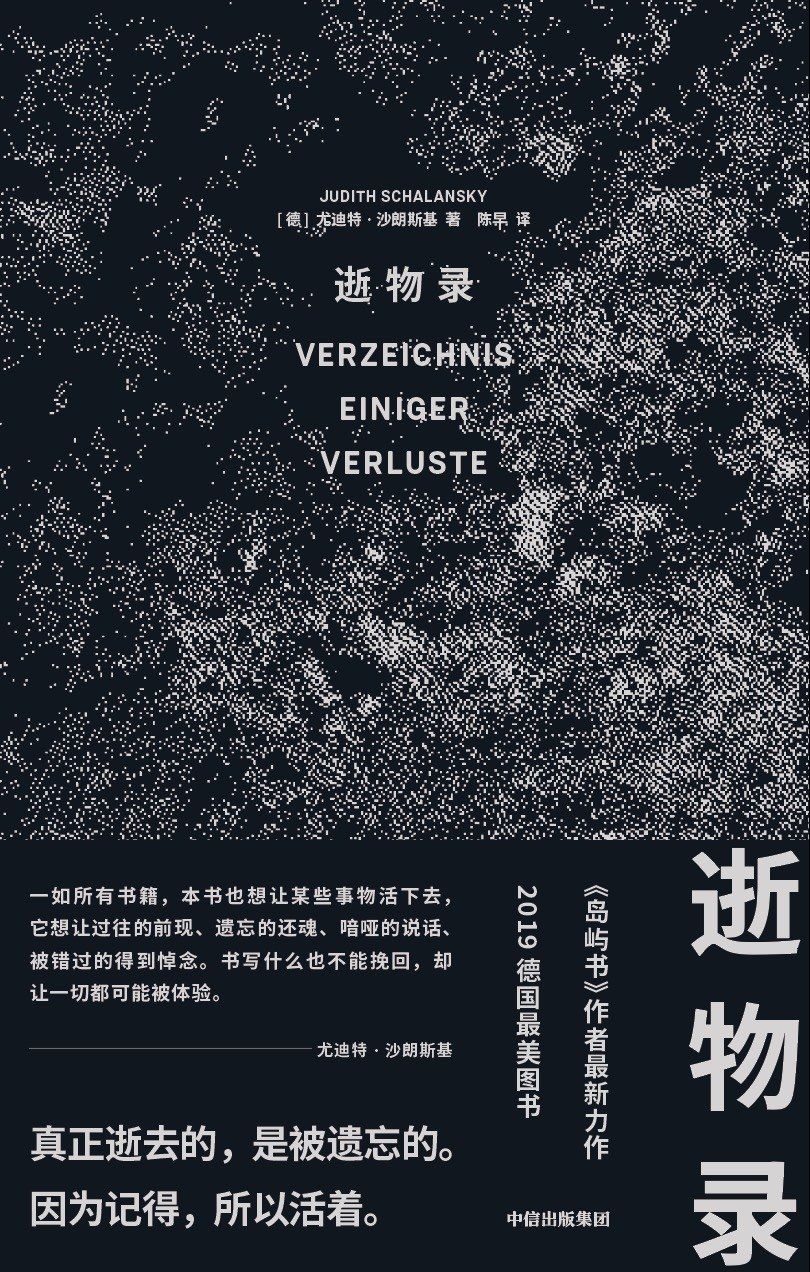
《逝物录》(德)尤迪特·沙朗斯基 著
那些质疑该书“矫揉造作”的阅读者显然无法理解作者面对消逝痛彻心扉的“怀旧”心绪,如她在书中所言,“也许幸运的是,人类并不知道他们已失去哪些伟大的想法、何种摄人心魄的艺术品和革命性成就,不论它们是被蓄意摧毁,还是在时间的流淌中单纯地销声匿迹……不少近代西方思想家却诡异地在规律性的文明没落中看到一种理性甚或疗愈的手段。就好像文化记忆是一种世界生物,只有活跃的新陈代谢才能维系其生的功能,每次吸收养分都要先消化和排泄。”沙朗斯基拒绝此种“新陈代谢式”的狭隘世界观,她认为,“人类——因深信他们出色的创造力可靠无误而饱受愚弄——将再次体验到无知最恐怖的后果”。
与沙朗斯基抱有相同想法的还有包括多位重量级学者、艺术家、建筑师在内的《旧物录》的作者们。他们用85个消亡之物的“失败”,回望文明与科技发展的“旧故事”。这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提醒人们,那些呈现技术“童年时期”的消亡之物,代表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对身体、技艺、美、艺术、交流、运动、休闲、爱、文化身份、自然和人工智能的不同态度,所谓的“失败”只是胜利者的视角。当人类“怀旧”之时,会认识到,一种不同于“进步”“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认定逻辑,它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论的线性叙事背后的危险,从快节奏、高强度、高密度的当代生活中抽身,看见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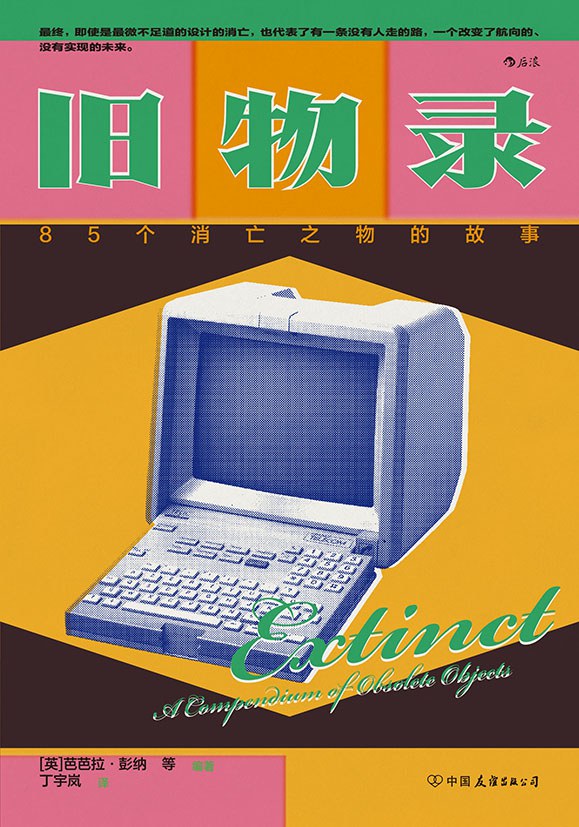
《旧物录:85个消亡之物的故事》(英)芭芭拉·彭纳 等著 丁宇岚 译
记忆中的时代图景
“我们不可避免地活在赛博时代,那些原本最熟悉的寻常日子,正在尘封中成谜,并被轻巧地抹去。”“80后”历史写作者、媒体人薛易在新作《弹幕书》中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具体生活,对他而言,这本书是以个人视角切入时代变迁的一次新尝试,它记述了1984年到2003年的自己。1984年他上了村里的育红班,2003年他大学毕业,户口从农村迁入城市……这期间的时代变迁令作者感喟:互联网加速改变了世界,众多“熟面孔”纷纷凋落,当年费孝通先生关心的“文字下乡”问题,似乎已被智能手机消解。当乡村的老人和孩子将短视频刷得飞起,算法精准算到了每个人头上,乡村记忆也随之被重构……《弹幕书》中着重于年少生活的细节追忆,照他的话讲,是充满童趣的书写。而书中还有大量留白,给予50位出生于不同年代、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们的评点、分享与感悟,成为书页的重要部分空间,新的读者阅读时也可以继续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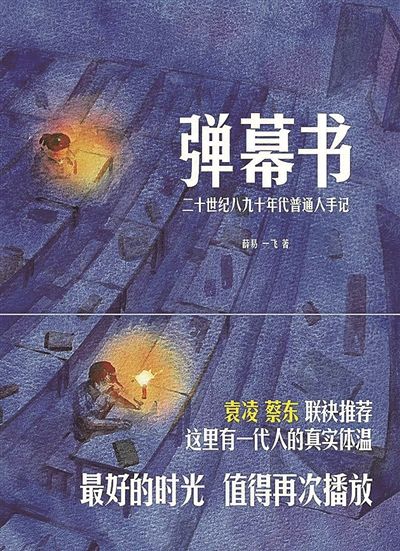
《弹幕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薛易/一飞 著
一本作者与读者共创的溢出纸面的怀旧书,留下一个时代的集体生活缩影,而或许正是这些保有丰富个体经验与细节的带有温度的“怀旧”,共同汇聚了一个逝去时代的鲜活图景。
故宫学者祝勇,今年也出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之作——《从故乡到故宫》,从沈阳军区家属大院里的童年趣事和见闻写起,沈阳的圈楼、大院的邻居、冬季的滑冰场、露天的电影院,还有第一次看到故宫时的震撼,一本小书里也潜藏着20世纪80年代一座城市市井生活的变迁还有一个成长中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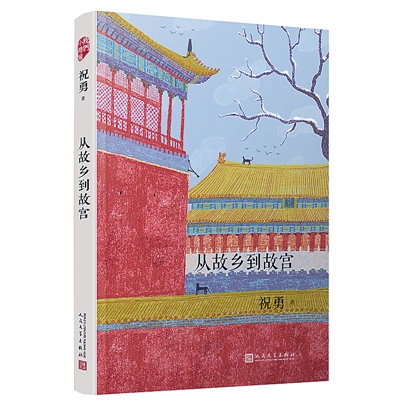
《从故乡到故宫》祝勇 著
从2013年开始,“99读书人”策划出版了“我们小时候”系列丛书,当代华语文学界的大作家集结,张炜、王安忆、迟子建、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纷纷写下自己的童年回忆,留下一个时代的“旧照片”。祝勇的《从故乡到故宫》是这一系列的第十部作品,他在书中写道:“从故乡到故宫,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个少年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坚守理想的成长轨迹。”
怀旧的书写不仅存在于非虚构的表达中,也成为虚构类叙事的主题。读者熟悉的“鬼吹灯”系列盗墓小说的作者天下霸唱,转型推出了新长篇《马路吉他队》,小说分为两季,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起,代表着时代情绪的流行音乐,成为作家怀旧的载体。“我特别怀念那个时代,那是我的少年时代。”天下霸唱充满了讲故事的热情,尤其关注那些时代变迁中的小人物。《马路吉他队》是一个关乎热血、梦想、岁月、激情般酣畅淋漓的故事,他解读自己的创作初衷:“想用吉他弦当针线,把那些碎布头似的时代声响缝成件百衲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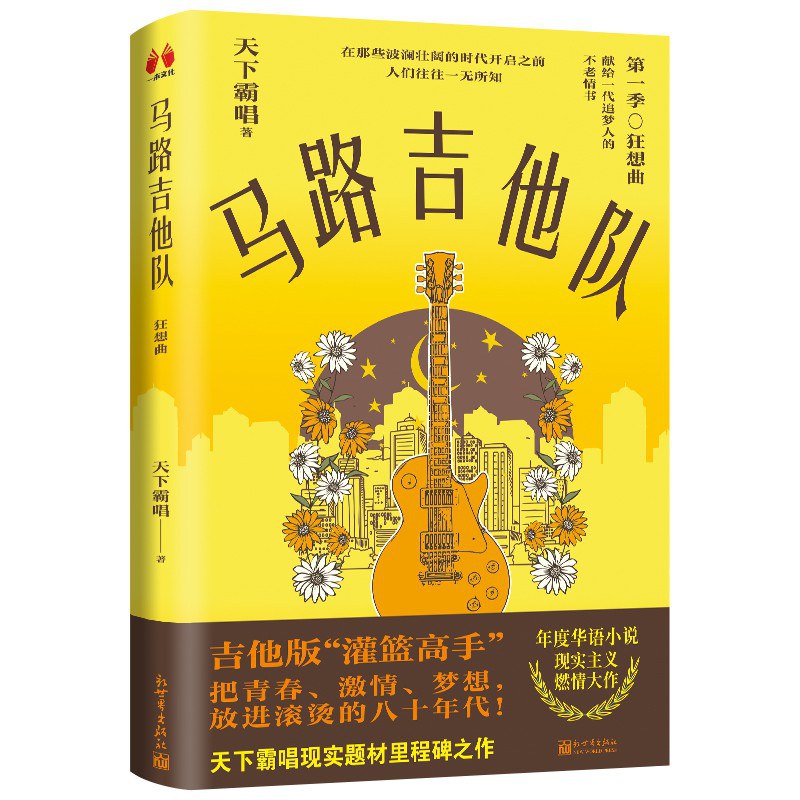
《马路吉他队·狂想曲》天下霸唱 著
《马路吉他队》里有穿皮夹克倒腾打口带的小年轻,军挎包里揣着“崔健”和“童安格”;包子铺师傅也能在吉他上扫出惊涛骇浪;还有揣着琴扒火车的草台班子,哪怕吃三天盒饭也要唱一首《大约在冬季》……天下霸唱说他所讲述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千万个在生活这条大河上甩出水花的人们的倒影。
“怀旧”即“疗愈”
与其说“怀旧”是写作者从当下一味“革故鼎新”的新世界中短暂抽身的避难所,毋宁说“怀旧”正是他们于时间演进中的情感堆积与宣泄。在记忆博物馆这个规模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的机械运转中,积蓄已久的情感总免不了喷薄而出,以其美好与澄明疗愈众生。
今年作家肖复兴有两本“怀旧”小书面世:《我的学生时代》记述亲情的热流、友情的纯粹与青涩的情愫,成长中的烦恼与遗憾、阵痛与迷茫,在记忆中去粗取精,时至今日,感知的皆是暖意;《一年好景君须记》则书写生活里那些微小璀璨的瞬间,从北大荒的雪夜到老北京的胡同,从少年宫的乒乓球室到异国的街头,还有暴风雪中的倔强、旧友重逢的温暖、陌生人的善意、不如意的生活和芜杂心绪中的点点诗意……“肖氏怀旧”自带疗愈功能,抚慰喧嚣中所有向内追寻意义与沉静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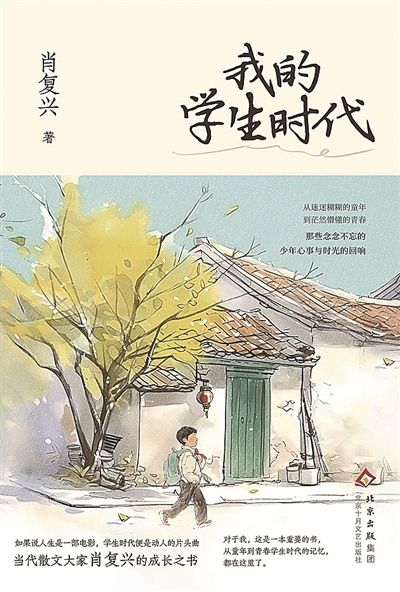
《我的学生时代》肖复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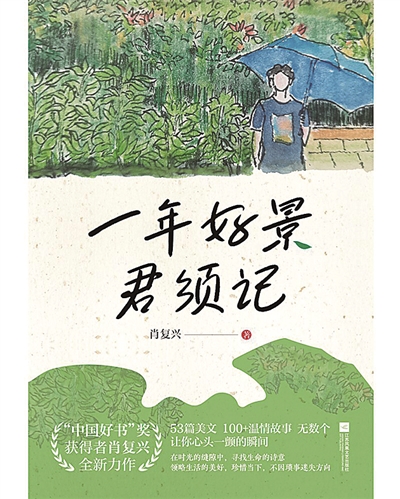
《一年好景君须记》肖复兴 著
怀旧的思绪中,故乡无疑是一个关键词。散文作家韩浩月《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是他对亲人、挚友和故乡朴素而坦诚的追忆,他说,“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才有往事”;“要是没了往事作为注脚,人也许会失去出处、根基与故乡”;“那些过往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终将在人生中的某一阶段化解,转变为深沉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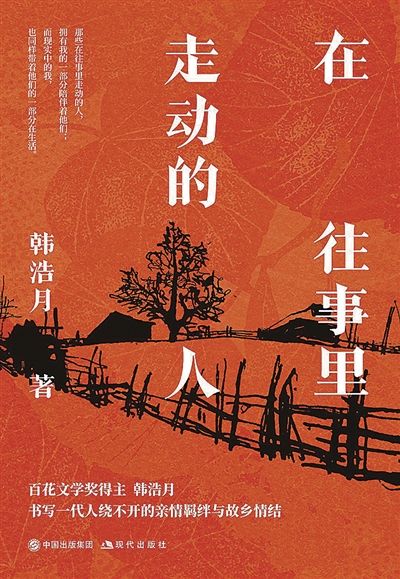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韩浩月 著
不久前漫画作者李宁静带着她的漫画书《我想记得的小事》来青岛进行了一场图说“怀旧”,那些同样饱含细节的插画,始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让读者将记忆的碎片重新拼装为我们共同的旧时光:一个普通女生“小李”从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明亮又苦涩的青春期,来到难搞的成人世界,她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李宁静说,当我们阅读过去,阅读那些细微小事,那些一不小心就会忘记的心情,然后释怀,也就更理解了一点现在的自己。而“怀旧”,正是想从过去的自己那里,借一点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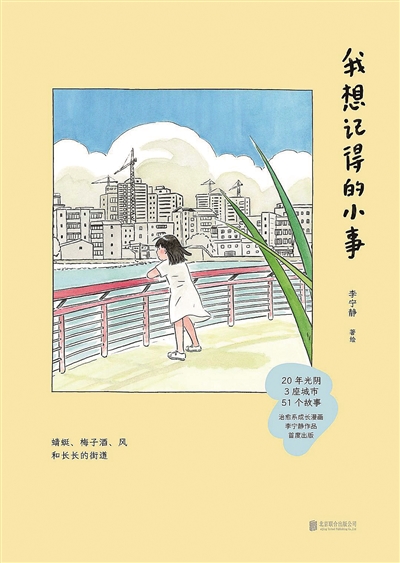
《我想记得的小事》李宁静 著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2025世界读书日
青报书单 - “怀旧”之书
《逝物录》(德)尤迪特·沙朗斯基 著
陈早 译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20版
《旧物录:85个消亡之物的故事》
(英)芭芭拉·彭纳 等著 丁宇岚 译
后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5.02
《我的学生时代》肖复兴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03
《一年好景君须记》肖复兴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04
《弹幕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
薛易/一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04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韩浩月 著
现代出版社2025.01
《乌乡薄暮》周蓬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01
《马路吉他队·狂想曲》天下霸唱 著
新世界出版社2025.04
《我想记得的小事》李宁静 著绘
铸刻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版
《从故乡到故宫》祝勇 著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03
青岛日报2025年5月22日11版
(点击版面查看更多内容)
责任编辑:吕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