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如何理解与重述一段战争史——
触摸历史褶皱中有温度的人
今天我们如何来理解与重述一段历史,一段战争史?
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说,“每个人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它们共同构成“复活一段过去岁月”的路径。以赛亚·伯林更认同文学对于第二层次的彰显。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上半年出版的有关那段严肃历史的书写中,对于第二层次的深入探寻愈发丰富和鲜活——
在《光明与黑暗的辞典》中,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用二战阴影下四代人的真实故事,将那些隐入历史尘埃的家族记忆与历史记忆存续,这个关于胜利和同情的故事时刻提醒我们面对最黑暗的邪恶时人类所能展现的勇气。这是一场与作者共同经历的深刻的情感体验;在陈存仁绝版多年重版的《抗战时代生活史》里,我们看到那段历史中普通人真实且鲜活的生活面貌,动荡历史中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有时比谍战更加惊心动魄;余耕的《问鼎1939》中,小人物继续极端情境下的选择与嬗变,街痞与英雄,善与恶可能就在一念间;祝勇《国宝》中的故宫人那文松和叶梅《神女》中的巴东船老大覃九河,具体的人,于历史洪流中的生命意义,正是我们理解那段往昔岁月的另一个门径;而在《雀鸟与群狼的对决》《二战史诗三部曲》中,那些伟大历史时刻的关键人物的非虚构精微描摹,给予今天人们的,已远超对战争本身的认知,而更关乎人性的共鸣与共情……
在这些有关那段战争的叙事中,学者、作家房伟的修订版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无疑称得上“另类”。
房伟没有采取传统的历史线性叙事,而是打出了一套独特的文学“组合拳”,那些精悍却丰富的人物故事织就一张鲜活而新奇的“历史之网”,对“抗战”作出另一种全景式的理解与讲述。如作家莫言所言:他专心致志地以个人的感悟来塑造文学形象,把历史和传奇化作了一组战争人物的个体“心灵史”。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战争的细腻想象,写出了生命个体在特殊环境下的尊严、伦理与挣扎。
文学的情感力量、主观视角和超越历史的想象力,是否恰如以赛亚·伯林所认同的那样,更能触及冰冷史料无法抵达的历史情感和创伤,更接近于历史与生活的真相,也因此更为人们所共情?既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又是写作者的房伟在采访中并未直接给出答案,或许答案已在他的小说里了。短篇《五三》中,主人公以“房伟”的名字登场,道出有关历史的慨叹:“轰轰烈烈的大记忆过去了,零零碎碎的小记忆也终将过去。它们融合成一团团雾气……大记忆会在雾气中越变越辉煌,个人记忆却越来越稀薄暗淡。”或许这正是作家以文学、以零碎的小记忆不断“触摸历史的褶皱”、赋予历史、历史中的人以温度的缘由。
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我并没有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而是学术研究之际,接触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越发慨叹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书写资源如此丰厚……正是对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那些历史的褶皱和可能性,会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维度、生存勇气与时间的智慧。
探究历史幽微处的可能性
“我想写出那些人性基本层面的超越战争爱恨情仇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弥补战争创伤,走向真正的理解与交流”
青报读书:短篇集《猎舌师》修订版中增加了一篇《异生》放在最后,开篇《中国野人》也做了增补,这些调整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各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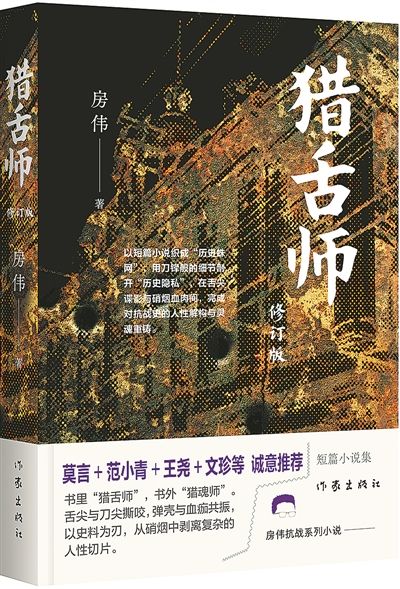
《猎舌师》(修订版)房伟 著
作家出版社2025.06
房伟:这两篇都是战争状态下,人在异国的故事,一个是中国劳工在北海道,一个是日本伤兵在河南,二者可以形成某种对照,也映衬着战争形态下人在民族国家情感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复杂体验。当然,主题还是有所区别,《中国野人》赞颂的是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坚韧生命力和顽强生存意志;《异生》则是批判战争对日本人的异化,从中国人对伤兵的收养上,考察中国人的宽容和人道情怀。从这一点而言,二者最后的落脚点,也都还在中国。
青报读书:这两篇小说是否都有人物和事件的原型?创作中有哪些震撼和思考?
房伟:两部作品都有原型,一个是山东高密被日本强征的劳工刘连仁,另一个是被河南农民家庭收养的日本伤兵石田东四郎。两个人都曾流落异国,都曾被驱逐与迫害,也接受过善意的关怀。我想写出那些人性基本层面的超越战争爱恨情仇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弥补战争创伤,走向真正的理解与交流。
青报读书:以“猎舌师”为书题是因为最爱这一篇吗?还是因为它是这部短篇集里最具戏剧高潮的一篇?
房伟:这既是因为它比较具有戏剧性的冲突,也是因为它是比较好读的一篇。
青报读书:这部抗战题材小说集,2019年初版时就曾获得很高评价,有评论指出你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也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具体而言是从哪些方面发力进行探索和尝试的?
房伟:这组作品,一方面,是在历史的褶皱中发力,发掘历史的幽微之处;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历史真实性、细节性和历史的想象性的结合。
我的笔下,有大人物,也有八路军战士、国军士兵,还有日本军官、随军僧侣,也有伪军军官、维持会的灰色人物,更有很多大历史下的普通中日民众。这里有英雄、汉奸,也有战俘、逃亡者。我试图展示一些战争的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幽微深处的种种可能性。历史的幽魂无处不在,它们不知何时就会从历史的深处冒出,成为人世的潮水中,飘荡无定的塞壬的歌声。
写出历史的复杂与丰富
“我们的历史文学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古为今用’与历史的肆意颠覆之间两极振荡”
青报读书:后记里,你说中国人很难从“常识”角度理解“历史中的人”,并对中国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太过拘泥史实,缺乏想象力和独创性”提出批评,这是选择以具体的人物故事编织“历史之网”的缘由吗?又是否意在以此解构线性的宏大叙事?
房伟:历史在中国文化之中,背负着太多沉重的东西,由此,中国史传文学有着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也导致进入现代之后,能客观地反映历史复杂性的作品比较少,我们的历史文学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古为今用”,与历史的肆意颠覆之间两极振荡。
青报读书:关于抗战的历史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历史成为您写作深耕的一个大类,从早期的纪实作品《屠刀下的花季》到抗战系列短篇的创作,再到长篇小说《石头城》。对于这段历史的文学性讲述何以对您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房伟:我从小喜欢军事历史文学,也有点英雄情结,算是个“伪军迷”。硕士毕业那会儿,还想过去某军区干文职,但眼睛近视,身体素质也不过关。一方面,战争文学能最大限度地表现文学的力量感,以及人在生死之间的强大意志与生命激情。中国人近百年的战争史,就将中国人的感时忧国精神进行了具体体现。当然,从比较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出发,战争也造成死亡与痛苦,是人类悲剧的源泉。我又是反对战争的。我觉得,战争文学的丰富性,也比较能体现中国故事的主体性。
青报读书:你的小说特别注重细节的真实性,比如淮扬菜的烹饪,城市的空间布局等等,这些物质层面的考据是否也是对抗你最为不齿的“神剧式”书写的一种文学策略?
房伟:真实性是文学的基本美德,历史小说更是这样。这一点我比较赞成马伯庸、龙一等历史作家,让读者信服,首先自己要在情理与事理上说服自己。
发现史料中的鲜活气息
“史料有时会成为一个细节,有时会引爆想象的开关,关键要看死的史料,如何与活的文学形象思维遭遇”
青报读书:你说过,最初的创作冲动并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对史料的兴趣。你的小说创作都是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在你看来,这些史料在小说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房伟:史料有时会成为一个细节,有时会引爆想象的开关,这个不好说,关键还是要看死的史料,如何与活的文学形象思维遭遇。
史料蕴含着一个时代最原始的细节,它们仿佛是一块块琥珀,将一个个历史瞬间定型,留给后人无数秘密去揣摩。站在一堆史料面前,就仿佛是站在一个个历史瞬间的现场,它把历史敞开来,让我们在那些褶皱之处,看到一个个心灵的喜怒哀乐,体验时代独有的气息。史料其实就蕴含着一个个“未成型”的小说。
青报读书:《鬼子妮》《小太君》和《五三》都是发生在济南的故事。《鬼子妮》里的老中医让人联想到曾经被媒体报道的山崎宏老人;《小太君》里对端午节、济南府“凤蓉街”的描写很鲜活;《五三》里竟然出现了你本人的名字,让人不禁想追问里面是否真有家族的记忆?
房伟:这几个小说,都与我的济南生活经验有关。《鬼子妮》是一个中日混血女孩的故事,是我在看山崎宏的纪录片时想到的,这样一个后代,她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会遇到更多的故事。《小太君》则有聊斋气息,纯粹虚构。《五三》有我爷爷的影子,他当时正在济南开小饭铺,亲历了惨案。
青报读书:书中涉及的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塑造他们时是否比那些纯粹虚构的人物更加困难?
房伟:也还好。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主要看把握的角度,我想还是要贴着人物写,从历史人物的遭遇,性格与历史语境,贴切地想象他的内心。
青报读书:看过一篇评论,说你在小说感性创作中也不时露出学术人的智性“马脚”,如在《幽灵军》里,随军和尚在心里默默对中尉大发同情,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中国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你个人认同理论研究者的身份对创作者产生的影响吗?另外,作为作家王小波的研究者,他以及他的作品对创作又有哪些启迪?
房伟:个人没想那么多。我写作是出于热爱。我是业余作者,我的专业是大学教书匠,我觉得表达得畅快,就是好的。至于学者的那些思维,可能会有遗留,这当然是要注意的,文学创作的逻辑,与理论思维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也不必刻意删减,因为它就代表了我个人独特的印记。
青报读书:据说《猎舌师》这部小说集的日译计划已在进行中,想知道之前在写作时是否有考虑到日本读者的接受度,比如小说中对“加害者创伤”的描写尺度?
房伟:我讲述这些抗战故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方面,我觉得有个基本立场问题,即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反对不义的杀戮与征服,另一方面,中国人要有胸怀与担当,当我们能正视敌对方的内心,正视他们的想法与复杂性,也就表明我们在心理上超越了“受害者情结”,真正从一个理性的强者角度,看待战争对所有人的伤害。战争不仅伤害了受害者,也伤害了加害者的善良,扭曲了他们的人性。总之,历史还要向前看,铭记历史,是为了制止未来的侵略战争,珍惜和平发展,促进两国的和平交流与理解。(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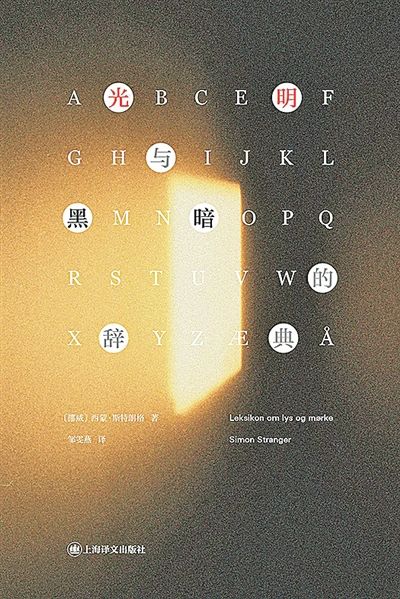
《光明与黑暗的辞典》(挪威)西蒙·斯特朗格 著 邹雯燕 译
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04
一本有关家族记忆的辞典,讲述战争如何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包括建筑、物体和人。不寻常的命运带来的苦难并未因其终结而终结,而我们能做的即是跟随作者重新经历一场深刻的情感体验,记住那些不再在这里的人,让他们的故事永垂不朽,并认识到我们正是由自己的过去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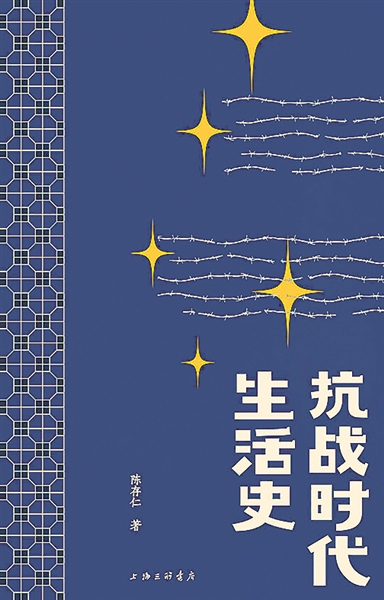
《抗战时代生活史》陈存仁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5.06
一名医生亲历抗战的八年手记,一个普通人在沦陷区提心吊胆的日常。一本绝版多年再版的非虚构经典。也许只有在读过这本书后,国人在那场战争中的生活面貌,才真正从历史中重新站立和鲜活起来。而我们才会发现,动荡历史里普通人的笑与泪,有时比谍战剧情更加惊心动魄。

《国宝》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03
故宫文物南迁的文学叙事。作者此前写作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这部建立于真实历史资料和档案之上的60万字的长篇,以“一家之离散”见“一国之荣辱”,以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见国格,亦见大历史中的真实与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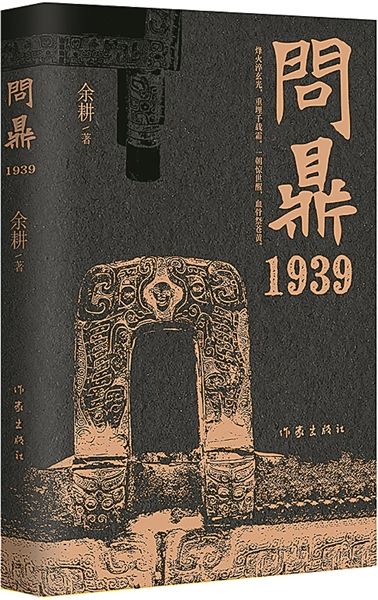
《问鼎1939》余耕 著
作家出版社2025.05
从街头混混到乱世枭雄,充满悬念与冒险的古玩江湖与残酷的战争风云交织的背后,最终将是极端情境中具体的人的选择。当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会发现,历史的底色正是人性。不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作者也延续着他一贯的对于大时代中小人物命运的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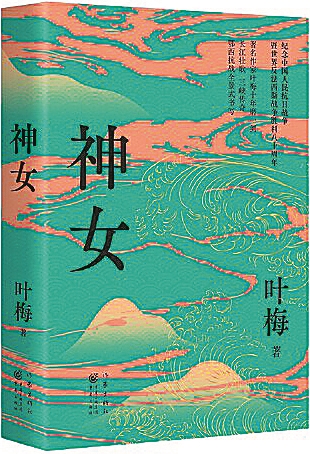
《神女》叶梅 著
作家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25.06
以巴东船老大覃九河一家为线索串联鄂西抗战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在个体命运之于历史洪流的抗争之外,亦提供了独特的地域视角,如作者所言:这是我对长江文化、三峡文化的一种礼敬,只是我从滔滔江水中舀出的一瓢水。如何书写三峡,如何书写长江,构筑新时代文学的大厦,我们还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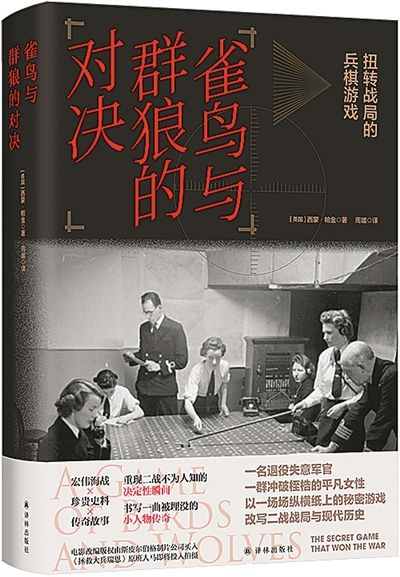
《雀鸟与群狼的对决》(英)西蒙·帕金 著 周媛 译
译林出版社2025.02
一群大多未满20岁的年轻女孩,于决定战争走向的时刻,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通过兵棋游戏的推演创造了反败为胜的历史。这一平凡女性制造的英雄传奇,被遗忘半个多世纪后,在非虚构作品《雀鸟与群狼的对决》中得以还原和正名,而它的电影版权已由斯皮尔伯格的制作公司买入。她们的故事是对传统战争叙事的颠覆,也是对历史真相的郑重补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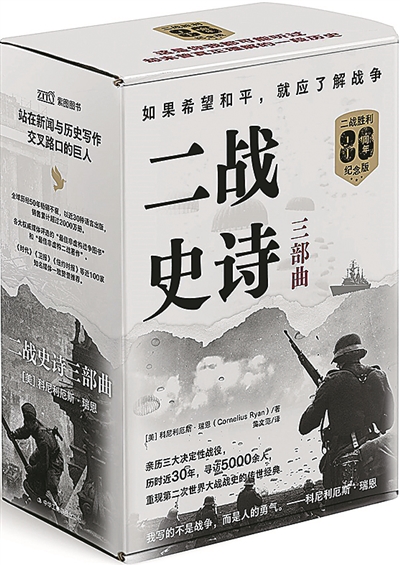
《二战史诗三部曲》(二战胜利80周年纪念版)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黄文范 译
紫图图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5.01
这套再版的畅销书解读了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读战争的缘由,那就是重回那些伟大的历史时刻,看历史中的人们如何抉择。这套《二战史诗三部曲》中没有概念化的史实、脸谱化的人物,只有基于各种史料、档案的人与故事。每本书都有一个主题,《最长的一天》关于“勇气”,《遥远的桥》关于“失败”,《最后一役》关于“生存”,即便是在远离战争的和平年代,它们依然与我们共情。

青岛日报2025年7月3日8版
责任编辑:吕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