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科幻作家双翅目的小说集《水星逆行》开启难以被精准归类的文本实验——
当我们以科幻的“新奇”理解世界
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提出的“新奇事物”概念认为,那些具有“前所未有”属性的事物,能够激发人类对未来的希望与行动力。“新奇性”推动个体超越现实局限,甚至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动力。此概念亦可为科幻文学创作提供注脚。
如果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算起,科幻小说的发展史逾200年,其间大师迭出,诸多有关未来的描述业已成真。不过,科幻文学叙事里的“新奇事物”并不仅仅意味着宇宙航行、外太空生物和硬核科技的成功预言,它亦存在于“科幻教母”厄休拉·勒古恩发掘的我们自身常识的死角与内心的森林中,也可以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造的历史时空,现实世界的一道隐喻……
当哲学出身的青年作家双翅目推出她近十年创作的第四部科幻小说集《水星逆行》时,我们不自觉地会将其归入上述作家的创作谱系,尽管她自称最为钟爱的小说作家是“在思想高度、结构复杂性与语言精度上皆无人能及”的波兰科幻作家、哲学家莱姆。
双翅目撬动读者认知边界的“新奇事物”包括:不同于传统科幻小说语言的“晦涩”的复杂化表达;将经典文学场景置于宇宙尽头量子片场的实验文本;以及在科学与“玄学”、传统与未来之间难以捉摸地摆荡式探索,她在现代人正在体验的事物里想象发掘新奇,提醒我们:引领人类走向未来的除了日新月异的科技,还有那些早已存在却常常被遗忘的过去。她将自己的创作尝试视为一种尚难在学术话语体系中被精准归类的文学性表达,试图以此创造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中文科幻的文本实验
“科幻文学可以成为一种丰富中文语言的可能性路径,它能够激发中文自身几千年演化的某些未被充分激活的部分”
青报读书:今年是你以双翅目为笔名写作的第十年,小说集《水星逆行》作为阶段性的总结,在作品遴选上有怎样的取舍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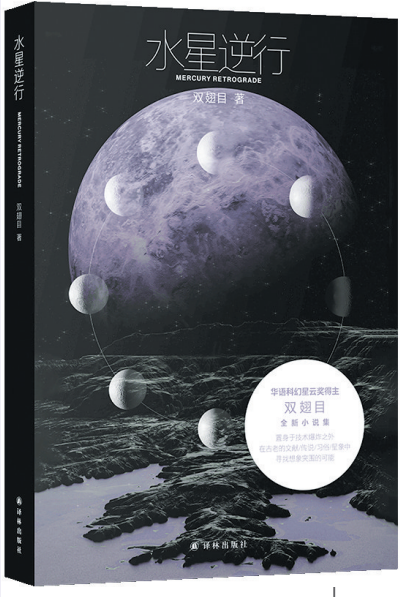
《水星逆行》
双翅目 著
译林出版社2025.01
双翅目:《水星逆行》收录的五篇中篇,其实是我在准备转向长篇写作之前,希望继续深入探索的一些主题。这些作品是一次具有节点意义的“收束”。我希望通过它们,定位我十年来科学与文学融合写作的一个阶段。最初创作时,我更多是出于一种直觉性的表达冲动,想把脑海中的科幻设想写出来。但当《水星逆行》集结成书时,我意识到它们的分量超出了我的预期,促使我更认真地思考科幻文学中“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青报读书:具体发生了哪些改变?
双翅目:从《公鸡王子》到《水星逆行》这十年,我出版了四本作品集,写作的核心诉求逐渐从点子的表达转向对文学性的探索(不过,我也确实从没放弃过某种“点子文学”)。换言之,科幻固有的实验精神——尤其是在问题意识和技术设定方面的实验性——在我这里逐步兼顾地成为对语言、形式和叙事结构再探索的平台。这种转向,也是在回应中国科幻的语境挑战。
青报读书:“中国科幻的语境挑战”具体是指?
双翅目:在我看来,中国语境下的科幻写作面临一个独特的语言张力:一方面,科幻文本中所使用的技术语言,大多源自对西方术语的翻译,往往带有“翻译腔”,在语言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上存在断裂;另一方面,中文自身拥有深厚的文学传统和形式潜力。那么,如何将这种带有技术性断裂的“翻译腔”与中文本身的审美和修辞机制相结合?这是我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我始终相信,科幻写作并不意味着必须服从通俗性或者牺牲文学性。恰恰相反,科幻文学可以成为一种丰富中文语言的可能性路径,它能够激发中文自身几千年演化的某些未被充分激活的部分。因此,在《水星逆行》中,特别是像“毛颖兔”和对老舍《茶馆》的改写篇章中,我尝试通过文字上的实验性去回应这种语言挑战。这种尝试既是出于写作技法的探索,也是对中文与科幻语言融合可能性的致敬。
哲学与科幻的互文式交锋
“我将哲学理解为一种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世界构建’活动,这也是我认为哲学与科幻之间最为本质、最具启发性的相似之处”
青报读书:你提到书中多篇作品都是搞专业、写论文写不出来时的“宣泄之作”。哲学以及美学这些专业训练对科幻叙事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科幻创作作为主业的“副产品”,又是如何作用于你的哲学思维和艺术审美的?
双翅目:我最初对哲学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科幻的热爱。大学时期,我主修哲学,逐渐意识到:无论是近现代哲学史,还是中西哲学传统、思想史乃至宗教史与社会史的学习过程,都不断呈现出一种“范式的转化”(或知识型的变化)的习得。这种思想范式的转换,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革命”极为相似。而在我眼中,每一次思想范式的学习和内化,都接近一次对科幻小说中“世界构建”(world building)机制的模仿和再习得。也因此,我有时将哲学理解为一种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世界构建活动,这也是我认为哲学与科幻之间最为本质、也最具启发性的相似之处。
近年来,国内对科幻的关注明显提升,其原因之一或许正是科幻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解世界的认知方式。在我的写作中,哲学与科幻的交叉是隐性基础。有时,我会借助哲学的理解框架去思考科幻写作的结构与主题。当然,我更倾向于探索那些传统哲学家未曾涉足,或尚未以特定的方式触及的问题。这是论文中无法论证,但小说可以尝试的表达。
我本人的学术出身为美学,因此在语言和文体方面,我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设想中的“先锋性”追求。我说过,中文在面对科技语言和翻译语言时,其文学性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在《水星逆行》中,我尝试在不同篇章中运用多样化的语言风格和叙述策略,这种风格的切换,有时会让读者感受到“难读”或“不易进入”的阻力。但这种探索恰恰是出于我个人在美学层面上的一种实践需求——一种当前尚难在学术话语体系中被精准归类的文学性表达。
经典戏剧的量子宇宙
“将原本属于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传统的话剧,置入一个‘宇宙尽头’的科幻框架之中。这种转化不仅是空间尺度上的扩大,也是在思想结构上对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的延展思考”
青报读书:《太阳系片场:宇宙尽头的茶馆》那一篇,对“涌现”场景的描摹,文字的精悍,读来很畅快。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或者说是陌生的熟悉感。评论将之定义为“折叠叙事”,创作中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双翅目:关于《太阳系片场:宇宙尽头的茶馆》的阅读反馈,我发现不同读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本身喜爱文学、对老舍作品有情感或研究背景的读者,往往会对这篇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相反就会产生距离感。这个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同时也恰好印证了你提到的“折叠叙事”的结构方式。
在这篇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中,我并非采取完全外向式、对外敞开的构建姿态,而是一种带有“叠加”意味的、向文本内部与向经典致敬的收敛过程。这个“收敛”是有层次的——
第一层,我尝试将老舍的原始文本直接“折叠”进科幻设定当中,保留其语言气质、人物逻辑和叙事框架;第二层,我试图将老舍所投射的时代反思,折叠进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结构、时代变迁的现实体会中;第三层,则是将科幻语言本身的陌生性与未来感,折叠进老舍那种时代气息与民间口语的原作语言中——
也因此产生了“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张力。这种语言上的张力,正是我试图创造的一种文体质感,体现了“折叠叙事”的实验性与它本身的风险。
青报读书:《茶馆》的掌柜在宇宙边界的量子片场迭代重生,这样的结局设置是否也暗示了今天我们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一种态度:经典文学必须经历“科幻坍缩”才能抵达当下人们的精神内核?你期冀读者给予这种改编重构怎样的反馈?
双翅目:我并不认为经典文学需要依赖科幻的路径才能通达现实。恰恰相反,真正的经典文本往往内蕴着某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它们本身就具备穿透现实表层、直指人类境况的深度。《茶馆》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历史感与时代深度的文本,其所内蕴的主题——“困局中的群像”“时代冲击下的人物命运”,都是难以改写的。
然而,从读者反馈来看,真正读过经典文学的人,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少。在当下这个以速度、算法和消费导向为主导的媒介环境中,“深度阅读”的习惯正急剧缩减,这一趋势比我们常说的“阅读量减少”更为本质和令人担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作为写作者的某种悲观情绪的来源。
这种悲观,并非针对经典文学是否还能与现实发生关联——我坚信它始终能。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现实是否还保有那种足以理解、承载、共鸣经典的感知结构。如果阅读的深度逐渐丧失,那么写作的深度也势必会受到侵蚀。人类今后的文学创作,是否还能达到过去那种高峰状态?这一点,我并不确定。可能不会有。
青报读书:说到对经典的重构,目前你的“太阳系片场”系列的两篇作品,一篇源于老舍的《茶馆》,另一篇源于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为何对戏剧经典重构情有独钟?
双翅目:首先,我尝试将原本属于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传统的话剧,置入一个“宇宙尽头”的科幻框架之中。这种转化不仅是空间尺度上的扩大,也是在思想结构上对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的延展思考。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分别位于“近现代转折点”的背景之下,它们的核心都指向了人类社会在遭遇历史断裂与结构变迁时,所面临的心理和制度性危机。将科幻的叙事嵌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将这些危机投射到更宏大的时空坐标中——这些问题不仅是民族的、时代的,更是“超越人类”的。
另一方面,“太阳系片场”系列改写所做的不只是题材或语境的科幻处理,而是一种文体上的反向实验。在当下的写作市场中,“小说剧本化”是一个常见的趋势,许多小说文本趋向于以剧本式的节奏与对白推进。我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将原本属于话剧范畴的剧作,以小说的语言、节奏、结构加以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我更直接地体会了“剧本写作”与“小说写作”在构造方式、节奏管理、语言密度和人物调度上的差异。
理性而非沉湎的“回望”
“这种回顾不是复古、不是怀乡症,而是寻找能和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思想结构相契合的、古典的思维模式”
青报读书:回溯经典、“回望”过去,已成为你的科幻作品的一个标签,《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一篇中作为“文眼”的毛颖笔,出自韩愈《毛颖传》,令人印象深刻,小说最后的表述也意味深长:“毛颖笔正静静逆流而上,他目送它,去了地下书库远古的未来。”对于未来的把握,要去过去的传统中寻。这部小说集的作品似乎都有类似的意味,这是你对于科幻题材的一种创新理念吗?最初明确这一方向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双翅目:其实我个人对“过去”的态度并非完全正面。过去所承载的许多思想与文化资源的混杂性,往往令人难以简单评判,也是我写作中反复纠结的问题之一。因此,《水星逆行》部分承担了一种“回顾性”的处理。但这种回顾不是复古、不是怀乡症,而是寻找能和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思想结构相契合的、古典的思维模式。
就价值立场而言,我更认同莱姆的观点:那些源自古老或神秘主义传统的观念,虽然在美学上可能富有魅力,但在解决当代问题时往往无能为力。真正的写作者必须正视当代现实的复杂性与困境,而非沉湎于对往昔的诗意怀旧。
事实上,在《水星逆行》中,我有意识地回避了对部分当代困境的直接描绘——这既是出于主题结构的考量,也与该作品集多数篇章的写作时间有关。这些作品主要创作于2021年到2022年之间。在那个阶段,我没有办法在创作中应对“当下”的结构性危机。所以《水星逆行》的“回望”也有逃避现实的成分。我也意识到,下一阶段的写作如果要回应现实,便必须从叙事与文本层面介入当下世界的种种撕裂与变形当中。这并不容易。
中国科幻理论诞生于五四精神,强调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批判和创造精神。时至今日,科幻不应只是传统的技术化叙事——那些崇尚暴力与阴谋论的、封建阶级色彩的、带有意识形态重压或性别种族歧视的成分——应当加以回避、反思,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写作予以拆解和超越。
我相信写作可以是一种既承认来源,又不被其所拘的行动,一种在深刻意识到局限性的同时,依然选择去创造的可能性。
对于复杂性叙事的偏爱
“我们完全有可能再次探索‘巴洛克式的中文表达’,探索新的语言结构与复调机制。”
青报读书:你推崇科幻大师莱姆的作品,《索拉里斯星》里的“无解之谜”,是否对《水星逆行》这篇小说的创作给予了启发?顺便问一下,你是一名不可知论者或者是神秘主义者吗?
双翅目:我非常喜欢莱姆。最初接触他的作品是在本科期间,读的就是《索拉里斯星》。这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在兼顾宇宙学尺度与人类存在论问题的同时,又维持了一种极高的文学性和哲学深度。我私下觉着:这是此类主题能够达到的顶峰之作,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超越它。
我自认为是“部分的不可知论者”,但并非神秘主义。我倾向于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可解释但不可穷尽”的体系:它的诸多机制可以被观察、整理、归纳,但某些层面上的终极性问题,我们或许永远只能承认其存在,但无法真正触及其本质。
举一个例子,莱姆的《其主之声》:在这部小说的结尾,莱姆安排了不同学者对宇宙展开一系列极为丰富的解释学式建构。读者在这一部分能够清晰感受到科幻小说特有的那种爆炸式的世界观堆积,以及宇宙理论的密集叠加。尽管它们在逻辑上存在冲突,但又在某些层面上表现出相互契合之处。这些看似对立却又部分融合的宇宙观并不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相反,它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反倒真实地揭示出一个事实:宇宙确实可以被赋予多种解释,但我们对它的最终理解依然处于不可知状态。
青报读书:多数读者对《水星逆行》文本的第一印象,是“无注释的论文”。你也曾说过自己的创作受到巴洛克哲学或美学所建构的无限的、嵌套式的、有着丰富情感的世界的影响。这是高密度复杂文本的缘起吗?
双翅目:有学者将“巴洛克”与“古典”提炼为两种根本性的思维样式,代表着人类理解世界的两种基本认知模型。古典风格所对应的,是一种基于稳定性与线性的认知体系,相比之下,巴洛克风格则更具复杂性与张力。这种风格上的分野,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对照,即莱布尼茨与牛顿之间的差异。尽管两人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但现代所沿用的微积分形式却更接近于莱布尼茨的表达方式与逻辑结构。牛顿主张时空为绝对存在,而莱布尼茨则认为时空源自物体之间的运动与位移,即时空是相对的。他的微积分体系正是建立在这种“关系性”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从哲学、文学还是视觉艺术的层面,我都更偏好巴洛克风格所呈现出的那种深度的复杂性与结构张力。在我看来,现代社会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某种意义上已经显著地进入了一种“巴洛克式”的表达范式。相较之下,文学叙事却并未同步进入这种巴洛克状态。尤其是在当代主流出版语境与读者接受机制的制约下,文学表达反而呈现出某种“去复杂化”的倾向,趋向更为简化、直接、功能性的语言模式。
莎士比亚的写作本质上具有极强的巴洛克特征——张力、转折、重复、夸饰、悖论并置以及音律的复杂性。在中文语境中,我最喜欢的译本,是朱生豪先生的版本。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及其剧作中部分诗化段落时,大量采用了楚辞风格的语言。楚辞的修辞特征——反复、铺陈、繁复的比兴结构与声韵运作——与莎士比亚文本的复杂性高度契合。这不仅展现了中文翻译对巴洛克风格的呼应,也提示:中文自身在历史上并非没有经历过“巴洛克”。
我们完全有可能再次探索“巴洛克式的中文表达”,无论是以楚辞风格为路径,还是探索新的语言结构与复调机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极具探索价值的方向。(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科幻书单(2025年4月-7月)
《造物须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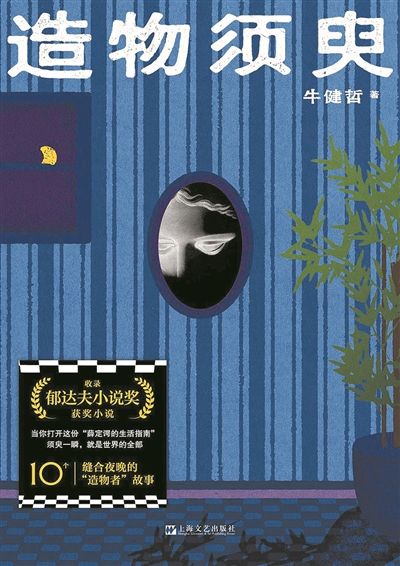
牛健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04
10篇造物小说,书写对人类精神世界深刻的好奇,以反讽的腔调陈述世界荒诞的事实。
《形式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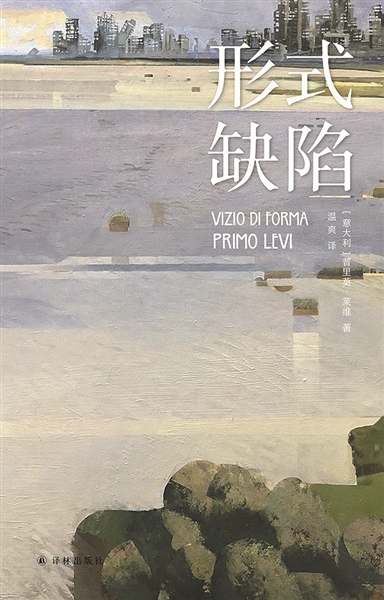
(意)普里莫·莱维 著 温爽 译
群岛图书/译林出版社2025.07
以20个写于“全世界最颓废时期”光怪陆离的故事,描摹理性沉睡时产生的怪物——人类文明与道德世界的形式缺陷。
《未来学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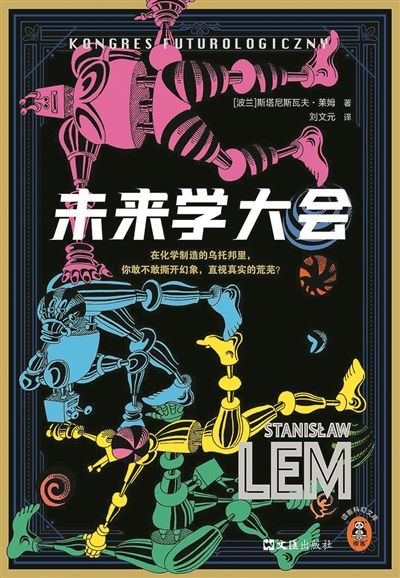
(波兰)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著
刘文元 译 读客文化/文汇出版社2025.05
青年科幻作家双翅目最推崇的波兰科幻大师莱姆的经典之作。提出了一个选择性经典命题:是直面惨淡现实,还是沉溺幸福的虚假幻象?
《时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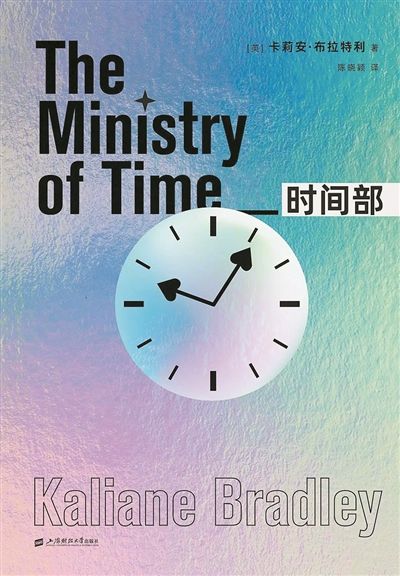
(英)卡莉安·布拉特利 著
陈晓颖 译
人天兀鲁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5.06
一部有关时空旅行的惊悚推理小说,烧脑又浪漫。
《异象》
(英)伊恩·M.班克斯 著 赵 阳 译
新星出版社2025.04
班克斯“文明系列”的经典代表作。人类末日危机中的自我救赎。
《孤注一掷》
(美)弗诺·文奇 著 胡纾 等译
八光分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06
硬科幻大师、雨果奖五冠王的中短篇小说集。文奇让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技术洪流中的位置。
《启示路》
G.E.M.邓紫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07
一个寻找人类终极奥义的故事,实则关于爱与探索。重要的是,它是名歌手邓紫棋的首秀,上市首日销量即破20万册。

青岛日报2025年7月25日10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