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努力理想化的生活——
过年:一年一度全民文化创造
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你是否已感受到年的气息?
学者冯骥才这样形容年的气息:它是“中国生活和文化中太陈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没尝过”。即便是那些沉溺于网络世界、不愿被传统束缚的年轻人,也或多或少因循在这积淀四千年的年文化的酒缸里,因为这是刻进每个国人骨子里代代相传的一年一度情感表达方式——
我们早已不再追问:为什么非要在除夕这天赶回家,回到父母身旁,回到家人中间;为什么分外在乎“家”,非要在此时此刻合家欢聚;为什么饺子是除夕餐桌上的主角;为什么全家要一起守岁;为什么除夕夜晚不熄灯,让灯光照亮屋中每个角落;为什么小孩不能哭;为什么压岁钱必不可少;为什么过年要穿新衣裳;为什么福字在此时分外耀眼夺目;为什么满口吉祥话,为什么到处谐音的吉祥图案:牡丹象征富贵,瓶子代表平安,公鸡寓意吉祥;为什么所有颜色中,大红色成了年的标志色;为什么平常看不到的神仙像,门神、财神、灶王、三星、八仙,这时候全冒出来了;为什么一听见爆竹声,心里就有“年的振奋”……这些刻进国人基因里的习俗,早已潜进我们的生活,成为年度“公理”。
没有任何节日可以像春节这样包含那么多精神、心理、追求、性情和偏爱,也没有任何一个节日,承载了几乎所有人间的美好期许与向往。而直至2024年末“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我们才得以郑重审视这一全民认同的“公理”,发现自己不仅生活在代代相传的传统中,更跻身于接续传承的创造中,一切正如文化学者冯骥才在《过年书》中所言:“大多数非遗的传承人是少数身怀绝技的传承者,春节的传承人却是全体中华儿女。而一代代中国人不仅仅是年文化的传承人,还是年文化的创造者。”
老先生提醒我们:全民努力过大年,一贯而下四千年,会是多大的文化创造力!正因如此,年文化才如此强大、深厚、灿烂,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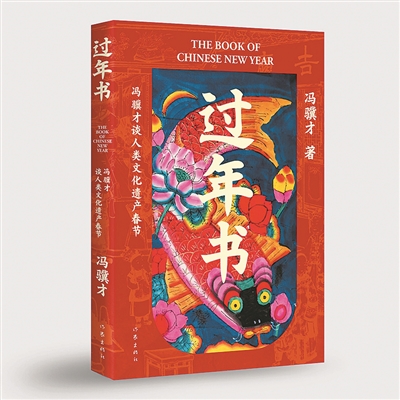
《过年书》冯骥才 著
作家出版社 2025版
“年”是一种强化的生活
长长四十天,天天有节目,处处有讲究,事事有说法”,由此构成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生活敷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作为春节申遗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如今已84岁高龄,2025年他推出了两部新书:系统梳理中国年文化的文集《过年书》和一部回望个人生命源头的随笔集《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两本书,一本关乎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另一本则关乎个人在天津五大道的成长涓流,而有关“年”的叙事在两书间达成了共振。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版
在《过年书》中,冯骥才回溯“年”的来源: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农家的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年在农闲时,便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了。或者说,年是一种强化的生活。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而在冯骥才看来,中国人真正崇拜的,不是所谓的太阳、龙、英雄,抑或祖先、圣人,而是生活本身!“过日子”往往被视为生存过程。在人们给天地三界诸神众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乃是企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又富裕的生活。这无非借助神佛的威力,实现向往;至高无上的仍是生活的本身。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等到过了年,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回到日常生活里,年的感觉也随即消失,好似一种幻觉消散。“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冯骥才说,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空竹、灯谜、花会、祭祖、拜年、压岁钱、聚宝盆等等这些年的专有事物,单是饺子,就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 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而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裕,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鸡与菊花喻意吉利吉祥……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生活敷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年画 缸鱼
一代代中国人,便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的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长长四十天,天天有节目,处处有讲究,事事有说法”,由此构成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
冯骥才的春节观,形成于天津这座市井文化兴盛之城,“五大道”与“老城厢”并存的独特城市格局,呈现于他的新书《清流》中。春节前的一次新书推介活动中,他曾言:“对于我,天津有另一种很特殊的魅力,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与气质,两种不同的文化。”他在书中描摹了自己25岁之前在“五大道”度过的人生,“五大道像一条河流,我的生命更像一条清流”。
在作家铺陈的1942年至1966年间的清流岁月长卷中,年的记忆如此深刻。他回忆起童年时殷实家庭过年“整车放鞭炮”的盛景,也记得普通百姓即使再穷也要“炖一锅肉,备两瓶酒”的执着。天津人“用画来过年”的传统,更被他视作一地文化气质的绝佳体现,曾在国际场合引来学者的浓厚兴趣。这些或许亦是他后来深潜进最本土、最市井的民间传统的缘起,《俗世奇人》中的鲜活人物,那些对年俗生动而充满感情的记述,其养分正来自这方水土。
回溯过年的快乐和意义
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在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地送走,或拿出去或直接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地迎进来。
20世纪50年代初,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最后写道:“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节。”原来,关于过年气氛的式微,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过年的快乐和意义,不论在任何年代背景下,都是共通的。

《北京的春节》老舍 著
译林出版社 2025版
历史学家顾劼刚在20世纪30年代为初版的《新年风俗志》所作序言中曾写到每逢节令的快乐:“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每逢节令,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红红绿绿地走着玩着,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这种快乐,仿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充满了高贵而又温和的意味;又仿佛这些花样是天上规定了的,有不能改变的意义。”
他还特别提及这种快乐空气存在的必然性:“数年前,我略略做了些民俗学的研究,才领悟到这种类乎迷信的仪式实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一个人在生命的长途中,时时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奋勉地从事工作,不灰心于一时的痛苦;而这种节令的意义是在把个人的安慰,扩充为群众的安慰,尤有重大的关系……就说新年吧,已经很劳顿地做了一年的工作了,该得喘一口气,尽力快乐一下,然后再整顿精神做第二年的事。这快乐,应当是什么呢?是赌钱吗?是嫖院吗?不是,如果如此,又流入个人主义了,又流入消极的人生观了。我们要掉龙灯,跳狮子,放烟火,点花灯,让大家一齐快乐,使得大家好提起精神,增进这一年中的生产的效能。”

《新年风俗志》娄子匡 著
领读文化/台海出版社 2023版
《新年风俗志》是绍兴籍民俗学者娄子匡的著作,1967年增订版面世时,娄子匡亦曾在自序中说:“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在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地送走,或拿出去或简直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地迎进来。这些迎新送旧的玩意儿。聪明人说它是迷信固然也对,不过不能说它没有意思,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化科学的人们。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的引言中说:宗教的冲动单只向着一个目的,即生命的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驱邪降福,虽然平常多是题在钟进士、张天师的上头,却包括了宗教仪式的内容,也就说明了岁时行事的意义了。”娄先生以宗教类比过年的意义,虽不确切,却也让人领会了他所谓的年的意义。书中坦言: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缘由,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
过年,这一全民参与的文化创造还将一年一度,继续绵延传承下去,而关于它的调查研究也将一代代延续下去,过年的形式和内容或许千变万化,但关于它所带来快乐和意义,精神与情感永续。
我们还需要年的仪式感吗
春节的复兴不是简单的“复旧”,而是文化上的选择与弘扬。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地保留和激活那些具有精神内涵的仪式与习俗,避免将传统“扔得太快”。
在春节作为世界非遗的荣耀与光环之下,一个现实问题也凸显出来:我们是否正在失去过年的“仪式感”?冯骥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认为我们的春节没有仪式感,不如西方的圣诞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的春节原本是有很强的仪式感的,但如今传统的仪式感已经被我们遗忘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失落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年有一个独特属性,那就是它是一种生活节日,支撑它的是传统民俗。“我们传统的年俗,并非可有可无,是有着很严格的程序的。比如在年的筹备上就有一整套要求。再比如,吃年夜饭之前必须祭祖,祭拜‘天地君亲师’,以焚香磕头的方式,向大自然、祖先、师长以及生命的传延表达感恩与敬畏之情。”他曾撰文回忆自己童年祭祖时的恭敬严肃,祭祖的先后要由老及幼,以体现代代传承有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推翻君主专制,‘君’被拿掉,但我们对‘天地’‘亲’与‘师’的敬畏却应该传承下来。一旦中断,传统的精神就会显得模糊。”

《风月同天:古代文化变迁中的细节》侯印国 著
领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 2021版
“祭祖之后是阖家团圆,今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顿团圆饭,其实没那么简单。一个家庭一年一度地把家庭的人气凝聚起来,和谐相助,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而且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凝聚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这时,全家人又不由自主地都会说上一些吉祥话,相互助兴,特别是让老人高兴。春节时,老人一定要放在‘最上面’的位置,桌上最好吃的菜要先夹到老人碗里,这种意识一年年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里。”
在冯骥才看来,民俗是一种亲和又美好的生活文化和生活情感。它是一种朴素的“仪式”,由衷地发自内心。它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内涵和情感内涵。
年文化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现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年轻人渐渐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二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多了,节日偏爱消闲,不愿再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三是年文化的传统含意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四是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有一种说法,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春节电视晚会和拜年三项内容,而拜年还在改变为电话拜年,如果春节晚会再不带劲,真成了“大周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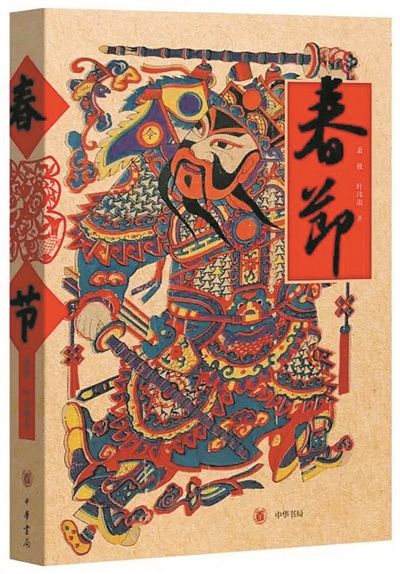
《春节》萧放 著
中华书局 2026.01
冯骥才认为,现在要紧的是,怎样做才能避免把传统扔得太快。太快,会出现文化上的失落与空白,还会接踵出现外来文化的“倒灌”和民族心理的失衡。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面对传统的急速流逝,冯骥才的选择不是停留在书斋叹息,而是“积极的应对永远是当代文化人的行动姿态”。他将这种抢在消失前进行的针对性抢救,称为“临终抢救”。他的行动既是具体而微的,比如抢救年画技艺,也是宏观制度性的,比如建议除夕放假、推动春节申遗,它们都已经成为现实。

《新年多吉庆 全家乐安然》 杨柳青古版年画
他认为,春节的复兴不是简单的“复旧”,而是文化上的选择与弘扬。社区与普通人能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地保留和激活那些具有精神内涵的仪式与习俗,避免将传统“扔得太快”。
“中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万里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而守护这座无形的长城,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觉与深情。(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6年2月11日7版
责任编辑:吕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