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珍贵的人世间,让文学告诉我们历史与时代的真相——
像小说家那样爱具体的人
贾樟柯的《风流一代》恐怕是2024年度最具争议的现象级影片了:一个女人从家乡出发,由北方到南方寻找青春时代的男友,过程孤独又落寞,镜头随女人的脚步掠过那些茫然、焦虑又真实的面孔,他(她)们组成或高歌或沉默的群体。全程没有起伏的情节,就连22年后的故乡重逢与别离都只有泛红的眼眶,克制的家常,最后终结于夜跑的人群,随女人一个意味深长的大口哈气戛然而止。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电影人想要留给我们的时代记忆,以貌似非虚构的虚构方式,呈现抽象的历史印迹里那些具体而微的生命个体的境况,时间在他们身上变动不居。
这仿佛也为今年出版的单行本长篇提供了一份概要。2024年,那些我们熟识的小说家们也在讲述着同样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
叶兆言的《璩家花园》,依然写他最熟悉的南京,一个名为“璩家花园”的老宅院里两个平民家庭、三代人的凡俗生活,堪比一部跨越70余载的平民生活史;
王安忆的《儿女风云录》,依旧是她熟悉的上海滩,围绕老爷叔“瑟”跨越70年的式微人生展开的,是一部上海小市民们的时代风云录;
格非的《登春台》,将虚构的时空置于北京,居住在春台路67号的四个人,他们的人生彼此独立又相互交叠,过去40余年间的命运流转和生存困境,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真实映照;
麦家的《人间信》,是发生在作家故乡富春江边的家族四代人故事,在这个20世纪中国江南村庄的微缩样本中,不被承认的创伤和未被看见的痛苦都是人生无法回避的永恒命题;
张楚的《云落》,一个叫作“云落”的北方县城的故事,独立女性野蛮成长的前半生,与身边一群平凡男女固守着各自的方向,在坚持和徘徊间组成我们的时代。
作家们从各自的时空和经验出发,跨越漫长的季节,为历史与时代作注脚,借由那些凡俗生活中普通人们的身体,发出对人世间一声克制的慨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而正是这些具体的人,组成了关于“我们”的抽象的群体记忆,正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日常,成为“我们”存在的意义,并由此构成“我们”的历史。
在《人的境况》中,汉娜·阿伦特写道:“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各自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2024年,在熟悉的作家虚构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看到另一种关于世界的经验与记忆,它们如此真实且具体,让人们不再感到孤独,彼此宽恕与共情,使我们成为“我们”。
在小说里叙述更加真实主观的历史
巴尔扎克说:小说就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定义放到叶兆言的《璩家花园》里则变得更加确实。
作为叶兆言的第14部长篇,《璩家花园》创造了作家作品体量与故事时间跨度的双重纪录,而它也被看作是将南京历史写到民国的《南京传》的续篇,囊括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对外开放、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革、发展经济、棚户区改造等等一系列历史纪年,“璩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点滴生活和命运起伏,那些重大历史时刻就在这一方天地里寻常人家看似不起眼儿的情感悲欢中悉数登场,一部七十余年中国老百姓的当代生活史呼之欲出。

《璩家花园》叶兆言 著 译林出版社2024.11
叶兆言提到,这部小说与以往自己的小说不同:“过去很多经验和想法,都是通过阅读才获得,它们可能会更客观,《璩家花园》则更主观,有太多的亲历,太多身边发生的往事。在写作的时候,这些人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身边。很显然,我正在和自己及同代人对话。”
而叶兆言的确也有着如巴尔扎克一样的追求——“做历史的书记官,时代的记录员”,他将自己所熟悉的小人物的个体经验,毫无违和感地融入大的历史背景中,书写的方式极其隐讳,比如:写“文革”后的高考,天井等一众年轻人准备参加高考,作家采用了耐人寻味的叙事方式:天井是在夜校上魏老师的课时,从一个向魏老师确认此事的同学那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而此时魏老师正在讲解鲁迅的《药》,便回答说,高考是治国的一剂良药,这个药可以医治很多毛病。就这样,高考与鲁迅先生的《药》以及国民性批判联系起来。
不久前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中,叶兆言处理难以言说的大历史与个体关系的高明之处屡屡被评论家和学者提及。具体到小说的细节中,作家写“文革”时期年轻人的残暴行为,刻意描写了一个淘气又温情的细节:突然获得的权力被年轻人用来整治一些不文明行为,如上厕所占坑死活不让的行为,他们用以改变这些不良秩序;作家还会选择特定的物象来呈现具体的历史时段,如1970年的物象是缝纫机,1954年的物象是俄语速成班,1976年的物象就是这个特殊纪年本身,“作家的叙事就像一股活水在历史的中心与边缘的生活之间流动”,他写章明与阿四谈恋爱,章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清华大学后信誓旦旦地对阿四说他不会变心,因此他抛弃阿四,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理由就跟历史中心的大事件相关联——他说,他正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总理逝世的活动,这个活动很危险,据此与阿四断绝恋爱关系,小说里这样写道:“天安门事件给章明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把自己弄得很神秘,弄得真像一个搞地下工作的革命者。”
宏大的历史叙事就这样压进看上去无比日常的琐细中。在《璩家花园》里,历史不只是布景,而是真正切入小说人物的生活,叶兆言还写到主人公天井和一众年轻人去接待“齐腰赛似裤”,在这里,指代宏大叙事的政治人物被老百姓赋予了市井化的谐音;还有伍师傅的退休与田中角荣的访华,看似两个维度的事情,在小说中却得以巧妙的连接,一代人的退隐和一个时代外交政策的逝去,这些隐隐的关联构成小说自始至终的书写方式。叶兆言没有正面书写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小说里却无时无刻不隐约感受到它们与普通人命运的连接,处处看到历史的车轮留下的时代印痕。
在虚实相间的记忆里回望自己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在提及小说与史实的关系时说:“我觉得小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类,它在真实和虚构之间不断地游荡,投射了以史实、以逼真为诉求的历史叙事所不及的地方。在大历史或正统历史涵盖面不及的地方,小说以虚构的能量填补了很多我们看待过去时经验上的黑洞,或者是我们认识论以外的种种不可想象的领域。”正是这些虚虚实实、缘于主观记忆的黑洞般的不可想象性,让我们不再纠结于人间事物的是非曲直,终究带着慈悲与宽容,与人生和解。这或许也是进入中老年的作家们普遍具有的历史观与写作心境。
王安忆在今年的新长篇《儿女风云录》里,再度进入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褶皱深处,为一位名叫“瑟”的普通人立传,此时距离《长恨歌》面世已过去了30年。这部故事时间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延伸到千禧年的小说,始终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像是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所进行的一次历史性回望。

《儿女风云录》王安忆 著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10
主人公“瑟”出身富门,少年时家道中落,单身北上学习舞蹈,吃尽大漠风沙,人情冷暖,直至中年,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沦落舞厅谋生……在国内度过大半生之后又和父母远赴美国孤悬海外。就像一个在舞台上不停旋转的舞者,不知何来,不知所终,只是兀自舞动,直至周围亲人不断退场,走出他的生活:父亲去了大西北,缺席他的成长;妻子在他“精神出轨”后带着两个子女离开去了香港。“瑟”在与两位女性“黑三”和“阿陆头”的交往中,意外收获了人生的开蒙和温暖。可惜,和黑三“方要下脚,又收住,滑过去,回到水平线上”……
王安忆借主人公之口惋惜道:“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浮泛中度过。浮泛的幸和不幸,浮泛的情和无情,浮泛的爱欲和禁欲。”宏阔的时间之河,承载的是“瑟”以及围绕他左右的不同身世的上海平凡男女的悲欢。他们的人生都有残缺,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小说中没有作为反转的“然而”,“瑟”最终戴上手铐,被拘留时,受托给他送些衣物和洗漱用品的是他的舞伴阿陆头。“到头来,还是阿陆头托得到!”小说的结尾,作家终究为“瑟”式微的人生留下一抹可以期冀的光亮。
“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寂寞,其实是金粉世界的局外人。”对于主人公的命运流转,作家没有给予评判,《儿女风云录》只是一面镜子,让读者看到时代中的自己——如风中的蜉蝣难以自控,经历悲欢、挫败,几经无意义的挣扎、跋涉,而这,或许就是作家交给读者的那份属于普通人的时代记忆。
时代与历史的伤痛无法避免,那么裹挟在残酷的命运之中,每个人又当如何选择?如果说王安忆书写的是一曲令读者沉思的怀旧挽歌,那么麦家在《人间信》中的时代回望则是一场救赎,是要与人生、与自己彻底地和解。或许只有在被放大的时间维度里,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感知那些微小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羁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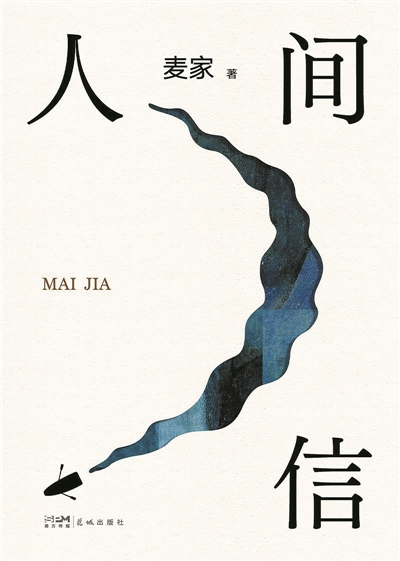
《人间信》麦家 著 新经典/花城出版社 2024.04
《人间信》记录一个家族四代人、连绵几十年的命运沉浮。这个被成长、死亡、离别、遗忘、悔恨、救赎所包围,又被爱恨无限交织的人生故事,在时间的催化下愈发真实。
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我”与亲人们重逢,于虚实之间呈现一个孩子成长的代价,这代价既是自己的,也是家族的,更是时代的。对于作家麦家而言,这是一部承载着个体与时代伤痛的小说,他以“我”的家族故事,发出对历史与时代的叩问,更是一次自我忏悔与救赎。
在普通人命运里给时代做精神分析
自“江南三部曲”以来,格非不再拘泥于知识分子叙事,而是更多观照普通人的生活。在《登春台》里,他以四个人物的命运和声,传达自己的人生信条。四人各自的故事更像是对人生不同阶段的隐喻,分别对应人生的四大命题:沈辛夷是存在之痛,窦宝庆是存在之罪,陈克明是存在之欲,周振遐是存在之寂。由痛而罪,至欲而寂,构成人生的循环终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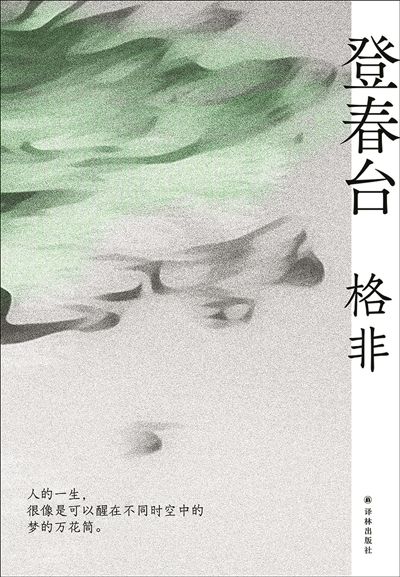
《登春台》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24.03
在格非看来,生存困境中的普通人,才是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登春台》似乎更多呈现了精神维度的时代书写,像是一次对时代进行的精神分析。小说中,有关于“拓扑学与现代物理”研讨会上的大量哲学研讨,从尼采、弗洛伊德到齐物论;听鹂馆里的读书会“明夷社”讨论的是黑格尔、谢林、禅宗和西蒙娜·薇依。这些充满神秘和玄学特征的哲学论道似与小说的主线内容相悖,却也是每一个正在或曾经跋涉的普通人无法回避的困惑。尤其是步入晚年的周振遐,长期被邻居的噪音搅扰,“稠密的人际关系”让他窒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群,让他厌恶。而他毕生所追求的,不过是“重新融入自然的心灵平静”……这个行至晚景,豁达但仍不免于困惑的老者形象,也更多承载着作家本人的心境,是作家与主人公一同追问生命的意义。
周振遐这个小说人物被年轻的文学评论者们看作是中国当代小说晚期风格的新范例。在年轻人看来,步入耳顺之年的作家们自带一种气场,运用时间的经验与阅历,提供文学表达的另一种可能。岁月与时代的印迹不仅写在他们脸上,更显现于他们具有人生哲学深度的创作中。在小说《登春台》的最后,四位主人公有和解、有期望、有温柔、有坚守,终于各自重建了自己与世界的连接。
作为70后小说家,张楚在《云落》中构建的县城普通人的世界则具有另一种气场,与小说的女主人公一样,看似混沌却活力四射,即便遇到危机也照旧生机勃勃,自然地展现欲望与渴求。云落,这座虚构中的普通县城里,普普通通的人在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时代的巨变中,他们的生活也被时代牵引,踉跄前行,悲欢相随。在张楚看来,这些普通人看似没有光泽,却是大的时代褶皱里最真实的人生风景。作家没有刻意去思考社会和时代的问题,而跟随那些普通人的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就在他们的故事命运中自然而然地展开了。

《云落》张楚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05
在作家格非看来,云落这个县城能够容纳更多作者想要容纳的事物,是一个足以承载中国社会全息式图景的地域,而他在其中感受到了作家的时代感与现实感。
在人与时代密切关联的人世间传承一种态度
曾有读者将《璩家花园》与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放在一起比较,对此,叶兆言的看法是,“我承认我写的也是人世间,但不同的作家眼中是不同的人世间。这是一本阐释时代和人的关系的书,人是渺小的,时代是伟大的,渺小和伟大都是相对的。”
叶兆言也曾多次表示,《璩家花园》是一个想留给女儿的故事,“我想把这本书留给女儿。希望有一天她会为此骄傲,自己的父亲竟然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作家想要传承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里,叶兆言以说书人的朴素口吻,将绵密的地理风俗、城市建筑、民情风貌铺陈进时空的缝隙与褶皱里,工人、保姆、小混混、教师、买卖人、警察、知识分子、干部等组成市井生活的群像,他松弛的语言背后是南京城七十年变迁里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历史波澜壮阔,社会日新月异,叶兆言注视的往昔岁月里,有费教授与江慕莲的才子佳人故事,李择佳与民有有缘无分的爱情,李学东、章明争夺清华大学名额的过往,还有仕途得意的高材生岳维谷,市场经济浪潮中下海的龚政策……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一以贯之,从不煽情,却让人五味杂陈,复杂的情绪,众多人物命运的悲喜,点到即止,没有渲染。
王德威在评论中说:“叶兆言恒以其世故练达的声音,娓娓讲述人情冷暖,世事升沉。我以为在描摹世情方面,他秉持了一以贯之的热忱。”人间值得吗?作家特别提及了小说的绝对主角——璩天井,他坦言自己塑造角色时对标了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和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书里许许多多的真人真事,唯独天井是理想化的,我对他充满爱。他做钳工做了一辈子,爱一个女孩爱了一辈子。他懦弱不重要,他不成功也不重要,他的爱有着落,他是最幸福的。”时世变迁,人心浮动,貌似呆傻的天井却始终未变。作为叙述者,叶兆言却并没有给出个人的评判,而是让读者自行评价,他只是将人物的命运展示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人生活方式、伦理模式,包括对家庭、亲情与爱情的丰富认知。如评论家们所言,“他写到繁华,写到生命的盛放,但最终都归于平淡……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实性,也是他最想传承给女儿的人生态度。
小说亦有悬置留白的未解之谜,叶兆言认为,“那些没交代结局的故事,不知道结局就对了,好多东西我自己都没搞明白,不是我没搞明白,是历史也搞不明白。我想描写时代记忆,真相如何不重要。”确如作家所言,“《人世间》是可说的,而这部小说更多是不可说的”。(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4年11月29日
责任编辑:吕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