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影灯下“追光者”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创始人谢立信
●如果说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肝脏移植是“玩大球的”,我们眼科就是“玩小球的”,但就是这么个“小球”移植的技术难题,全世界到现在都还没完全攻克
●如今,我国在眼科学领域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外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国外能生产的,我们也能生产。虽然我们并不是每一项都比国外强,但这种差距是锯齿状的,是各有所长的。可以说,我国角膜病的科研与诊疗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在某些领域已经实现了领跑
●很多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觉得人的角膜、生物组织工程角膜和人工角膜之间是迭代的关系,其实不然,三者的适应证并不相同,就像是汽车、火车和飞机同为交通工具,但应用的领域不相同一样
●当前眼科学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基因治疗、干细胞、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正在重塑眼科诊疗模式;二是转化医学快速发展,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周期大大缩短
谢立信,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创始人、名誉所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院长,主要从事眼科角膜病、白内障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是我国角膜病专业的领军者,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开拓者,中国眼库建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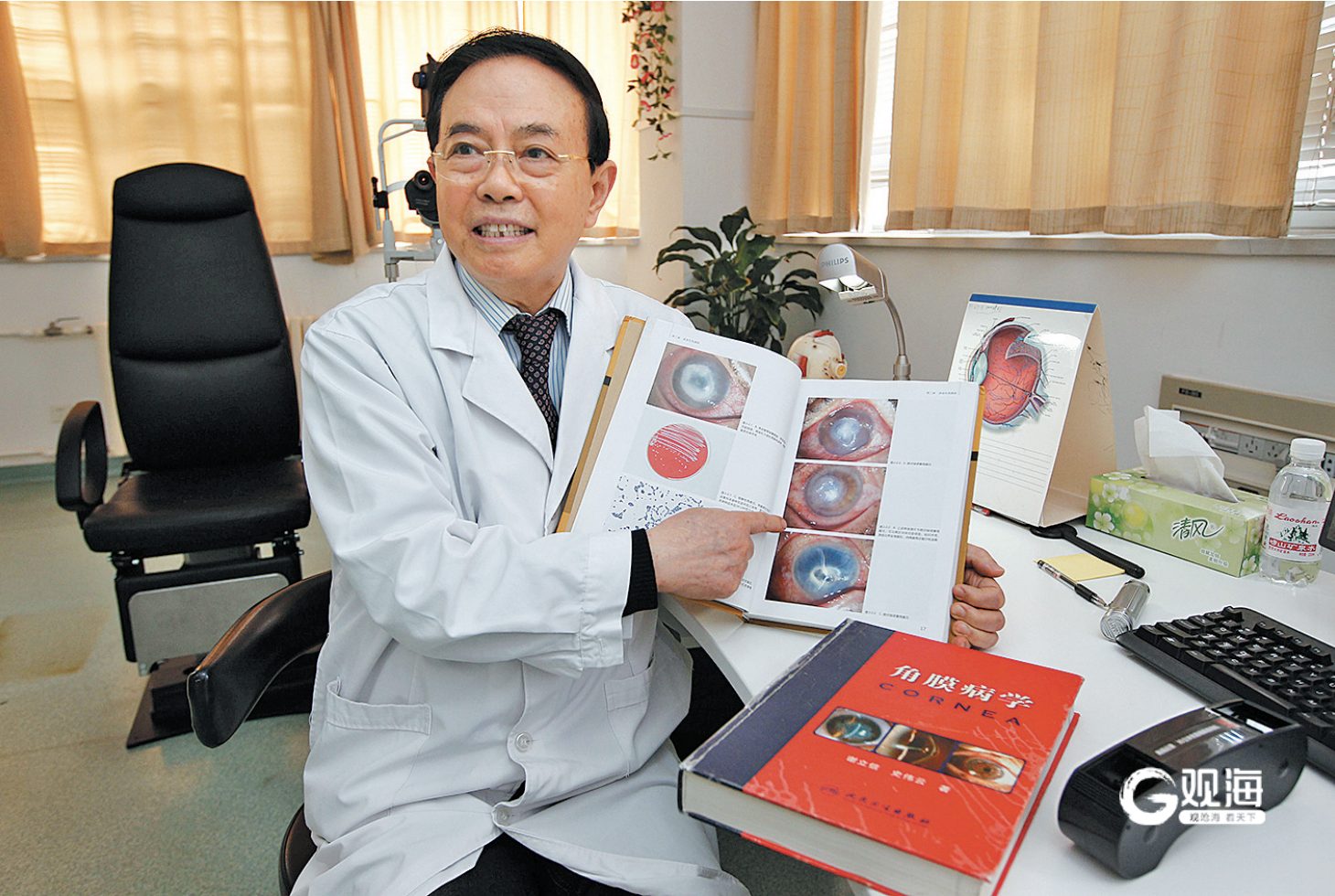
谢立信介绍角膜病的相关知识。
对于一个人来说,视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独立、尊严、工作和感受世界90%以上信息的能力。眼科医生,因此被称为“追光者”。
近日,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的无影灯下,谢立信凝神端坐,目光透过显微镜,如同进入以微米为计量单位的视觉宇宙,他的指尖轻抵显微器械,在薄如蝉翼的角膜上进行分离、缝合,极致精准地“微雕”,完成了一例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为因先天性角膜内皮营养不良几近失明的新疆患者重启清晰视界。
作为我国眼科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年逾八旬的谢立信依然精力充沛,坚持参与门诊、手术、科研教学、医院管理。在全国重要学术会议上,他对中国眼科学发展充满期望,提出了各种前瞻性、创新性战略观点。
“如果说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肝脏移植是‘玩大球的’,我们眼科就是‘玩小球的’,但就是这么个‘小球’移植的技术难题,全世界到现在都还没完全攻克。”谢立信如是说。“玩小球”的眼科医生和科学家,在追逐光明的路上,寻求着最精细的探索和最勇敢的突破,守护着每个人眼前最清晰、最珍贵的世界。

谢立信(左一)讲解手术要点。
从医从教60年来,谢立信从潍坊医学院的小研究室到如今国内外知名的眼科专业机构,从创建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到创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青岛眼科研究院,从发表第一篇中华眼科杂志论文到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他带领团队在追光的路上创造了中国眼科界诸多第一。接受记者采访时,谢立信一再强调:“科研工作要始终围绕国家和患者的需求展开,医学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人民的健康。我们不仅要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更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引领,真正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让更多眼疾患者受益。”
30多年“填平”中外眼科差距
记者:您在1965年从医,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只有一支手电筒、一台眼底镜、一张视力表。在那样匮乏的年代,您为何毅然选择角膜病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谢立信:角膜具有特殊性,它首先是眼部最重要的屈光间质,作用是将物体的光折射到眼后段的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像,因此,任何破坏角膜的透明性、形状、完整性的病变都可以引起视力下降。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面,是眼球抵抗感染及机械损害的主要保护屏障,如果角膜受伤,继而发生混浊、破裂或感染,会直接导致视力受损。
科研工作者在选择研究领域的时候,往往是从国家和患者的需要出发的。在20世纪60年代,感染性角膜病,尤其是真菌性角膜炎,是角膜致盲的首要原因。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在劳作中很容易被麦芒、稻穗等植物伤到角膜,一旦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就可能导致失明。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角膜病作为研究方向。后来,白内障成为全球第一位致盲性眼病,我又投身白内障诊疗的研究,在国内率先引进超声乳化白内障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并积极推广。
记者:1987年,您前往美国跟随世界顶尖的角膜病专家学习深造,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在两年后毅然回国发展?
谢立信: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在角膜病治疗领域的差距是“代际”的。可以说,当时外国医生用的是“洋枪洋炮”,中国医生用的是“大刀长矛”,这个“刺”在我内心扎得很深。我下决心,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我一定要回国投身中国眼科学的发展浪潮,为中国眼科学贡献我的全部力量。
记者:作为中国眼科学发展的引领者之一,您认为今天中国眼科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谢立信:我们经过30多年的努力,可以说已经拉平了跟其他先进国家在眼科学方面的差距。
当年,先进的设备我们可以花钱买到,但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和技术是买不到的。回国后,我组建了团队,奋力追赶。首先是推广显微手术技术,我们依托苏州医疗器械厂组织了大量的学习班和学术讲座,向全国的角膜和白内障医生介绍显微手术技术,如今眼科的显微手术已经在全国普及,成为眼科手术的常规技术。
发展眼科学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基础研究。我带领团队建立了眼库和实验室,通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在角膜保存技术、移植免疫排斥反应的防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如今,我国在眼科学领域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外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国外能生产的,我们也能生产。虽然我们并不是每一项都比国外强,但这种差距是锯齿状的,是各有所长的。可以说,我国角膜病的科研与诊疗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在某些领域已经实现了领跑。
比如,在角膜病领域,我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并论证了角膜内皮细胞功能失代偿的临床早期诊断标准,并提出了眼库供体角膜活性新的判定标准——“活性密度”的概念,对指导临床和提高角膜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具有重要价值。这项成果在1989年获得了中国眼科学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针对真菌性角膜炎,我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提出不同真菌菌丝在角膜内存在不同生长方式,根据这一理论用板层角膜移植术治疗真菌性角膜炎,一次手术成功率达到93%以上。该研究成果被编入2005年版国际权威性角膜病学专著《Cornea》。
角膜移植供体从捐献走向人工
记者:角膜移植手术作为角膜盲最常用、有效的治疗手段,从发明至今已逾百年。然而,人的角膜供体不足和掌握角膜移植手术的医生数量有限等问题仍然难以突破,我国在这方面是如何破局的?
谢立信:人的角膜如同相机的镜头,玻璃脏了、裂了,擦不干净就要更换。而角膜移植就是用透明、健康、安全的人体角膜、生物角膜或人工角膜片置换浑浊或有病变的角膜,以达到治疗角膜病、恢复视力的目的。角膜移植手术已经发明超过100年,我国开展角膜移植至今也近80年。在这期间,中国医疗科研工作者们聚焦角膜病的移植术式创新、并发症防治及角膜供体替代材料的开发研究,推动手术形式从原来的穿透移植和板层移植,过渡到如今的角膜成分移植,以最小的损伤实现了对患者视力最大程度的恢复。但即便如此,供体角膜严重短缺仍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长期以来,移植的角膜依赖爱心人士的捐献。但每位捐献者最多提供一对角膜,而且角膜是活的组织,必须在捐献者去世后24小时内获取,然后放在特制的保存液里。即使这样,它的最佳使用期限通常也只有一到两周,这导致角膜无法像血液一样建立大型“库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供体。流调结果显示,我国角膜盲患者有近400万人,而且以每年10多万人的速度在增长,但由于供体短缺,每年仅约1万例患者能够实现角膜移植,90%的角膜盲患者因等不到角膜供体而生活在黑暗中。
角膜供体匮乏,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技术方面的瓶颈。要想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要推动立法保障,加强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自愿加入到角膜捐献的行列中来。我牵头创建了国内最早的符合国际标准的眼库——山东眼库,帮助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在“离开”时为他人留下“光明”。青岛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截至目前,已实现角膜捐献2504例。这串数字意味着,数千名角膜致盲患者得以重见光明。
另一方面,医疗技术创新也成为重要的破局之道。比如,我在1981年研制出“人脐带血清角膜活性保存液”,可以有效地保持角膜的活性和透明度,效果达到国际水平,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五分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的史伟云教授做了进一步优化。2025年6月,我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角膜保存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使角膜的储存时间延长到2周左右,让更多爱心人士捐献的角膜得以充分利用。
角膜移植精确供受体匹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以前的技术条件下,一个角膜只能帮助一名患者,随着角膜成分移植技术的成熟,患者角膜缺失哪一部分,医生就可以从捐献的角膜中选取相应部分完成移植,一枚角膜就可以帮助更多患者重见光明。
但角膜移植术作为甲类组织移植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目前,全国能够熟练掌握技术并独立完成角膜移植手术的医生不超过百人。我国正在通过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角膜病专科医生的数量和水平,并鼓励医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和技术动态,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记者: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工程角膜和组织工程角膜领域的科研攻关取得了重要突破,2015年由您主刀的全球首例生物工程角膜移植手术获得成功,生物工程角膜已经可以替代人的角膜供体了吗?
谢立信:近年来,生物工程角膜和组织工程角膜等角膜替代材料不断研发和应用,为解决角膜供体匮乏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生物工程角膜研发是“十年磨一剑”的过程。所谓生物工程角膜,是指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制备的、用于替代人角膜的移植材料,目前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通过生物化学方法彻底去除猪等动物角膜中的细胞和遗传物质,仅保留天然角膜的胶原支架结构,从而让患者自身的角膜细胞依附其上,逐步“再生”成外观透明的组织。
我们团队从2005年开始布局相关研究,提出了胶体渗透压调节的脱细胞理论,研发出特异性脱细胞保护液。这种保护液能够有效去除猪角膜中的异种细胞和抗原,同时保持角膜基质的显微结构和透明度。经过反复的实验和优化,我们终于成功制备出了符合要求的生物工程角膜。2015年,我们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生物工程角膜移植手术,将生物工程角膜从实验室研究推向了临床应用。术后,患者的视力逐渐恢复,没有出现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
生物工程角膜的研发和应用,部分解决了材料来源问题,还避免了异种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已成为治疗部分角膜盲的有效手段,减轻了对捐献角膜的依赖。目前,相关产品已在全国500多家医院推广应用,使10万多名角膜盲患者重见光明。
但目前的生物工程角膜仍无法完全替代人角膜内皮层。生物工程角膜的另外一类组织工程角膜代表了更前沿的科研方向,其原理是利用干细胞技术、3D生物打印等在支架材料上培育具有活性的角膜细胞,以构造出更接近天然角膜的结构和功能。该项研究一旦成功,有望实现角膜的全层完美替代,彻底解决供体问题。
记者:近年来,大量人工角膜产品开始应用到临床,其中就包括您的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研制的国产人工角膜。人工角膜为什么如此被重视呢?
谢立信:人工角膜,顾名思义是指用人工合成材料制成的一种特殊屈光装置,用以替代病变后阻碍眼球光学通路的浑浊角膜,使患者获得一定视力。它的优势是,患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移植面积和厚度,不再受供体局限,而且可以终生使用。
很多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觉得人的角膜、生物组织工程角膜和人工角膜之间是迭代的关系,其实不然,三者的适应证并不相同,就像是汽车、火车和飞机同为交通工具,但应用的领域不相同一样。在角膜致盲的疾病领域,有15%的患者因为泪液、眼睑和眼球结构等原因,无法通过传统人的角膜或是生物角膜的移植恢复视力,人工角膜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之前我们没有国产人工角膜,研制国产人工角膜成为攻克让国内角膜盲复明“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中国人眼睛与欧美人存在差异,国产人工角膜需要根据国人眼球特征进行研制。人工角膜最核心的部件——镜柱,它仅有绿豆大小,需要车床在上面做复杂的雕刻,难度堪比在绿豆上雕刻一栋建筑。我们的眼科学科研团队和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先后攻克了工艺、材料、厚度、内应力等难关,自主研发的国产领扣型人工角膜实现了国产人工角膜“零的突破”,帮助一部分角膜盲患者重见光明。
记者:近年来,基因治疗不断突破,您带领团队开展的“角膜疾病的基因治疗”获评“2024眼科学中国十大原创进展”。未来,角膜病的基因治疗有什么样的前景?
谢立信:所谓基因治疗,是指将正常的基因导入人体细胞,从而纠正或补充基因缺陷和异常,达到治疗基因相关遗传眼病的策略。遗传性眼病由基因缺陷导致,往往表现为家族性疾病。此前,绝大部分遗传性眼病缺乏有效的根治手段。近年来,基因治疗在眼科领域进步快速,从细胞实验、动物研究真正走到临床试验,甲状腺眼病、先天性黑蒙等疾病的基因治疗取得突破,给遗传性眼病患者带来了重见光明的希望。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针对角膜遗传病的基因治疗方案正式临床。我们团队坚持面向国内重大危害眼病防治需要开展临床和基础研究,并积极推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在角膜营养不良和神经营养性角膜病变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研究进展,为未来角膜疾病的基因治疗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解决方案。
扎根青岛引领未来
记者:您创建的山东眼科研究所和山东省眼科医院,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眼科学发展的重要平台。请您谈一下这个平台对青岛、对山东乃至全国的重要意义。
谢立信:山东省眼科研究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眼科中心之一。它在青岛这片土地上闪耀着光芒,为当地乃至全国的眼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山东省眼科研究所下设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两家三级甲等医院,年门诊量超过80万人次,手术量超过8万台次。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重见光明。其中,外省患者占比达到25%到30%,彰显了该平台在全国的影响力。
在科研方面,我们的研究所建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这是我国眼科领域的重要科研平台。在感染性角膜病、复杂性角膜移植、儿童先天性白内障等领域的诊疗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们团队在这些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前沿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3项,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2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7项。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由院士领军,院士有效候选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领衔的创新团队,这源于对人才培养和引进的高度重视,我们努力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科研条件。截至目前,我们自主培养硕博士研究生530多人,他们将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全国各地,为当地的眼科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蓬勃兴起,科学探索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在您看来,眼科学工作者应该有一番什么样的作为?
谢立信:当前眼科学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基因治疗、干细胞、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正在重塑眼科诊疗模式;二是转化医学快速发展,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周期大大缩短。
面对这样的趋势,眼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能力,既要深耕专业领域,掌握眼科前沿知识,又要开放合作,主动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先进技术和方法。我们团队近年来积极推动学科交叉,与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精密制造等领域的专家合作,在人工角膜、基因治疗、智能诊断等方面不断实现突破。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临床需求导向、基础研究支撑、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思路,围绕重大致盲性眼病开展系统研究,一手抓基础创新,在发病机制、新型治疗靶点等方面寻求突破,一手抓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技术和产品尽快惠及患者。只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够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作出更大贡献。(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黄飞)

青岛日报2025年9月16日1版

青岛日报2025年9月16日3版
责任编辑:程雪涵



